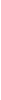恰空Chaconne12
盗文的都怎么了?请大声说出来
后来olivia告诉我的。她看到许念初和那女孩牵手,她们大概是已经在一起了吧。
所以,在我面前不承认有什么用?想瞒着我,又能瞒多久;就我们这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
她们到底从是什么时候开始暧昧的?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一遍遍复盘时间线。那次在食堂,她们是不是就已经开始接触了?所以,这就是她不肯对我说喜欢的原因吗?
因为她其实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渣女。
我甚至开始替那个女孩感到不值得。和这种人谈恋爱到底有什么意思?还不如买一个冬瓜抱着睡,至少它不会说难听的话,不会莫名其妙地作出伤害你的事情。然后,在她开心的时候,又若无其事地靠近你。
明明刚刚还在我面前和自己的女朋友亲亲我我,转头却又毫不避讳地打量着我,凑过来嘘寒问暖;看我一副不想搭理的样子,她就搬出“不是说好在外人面前要和睦相处吗”来要挟我,毫无边界感的对我评头论足。
我当然知道春装在哪里,我不是什么离了她就活不下去的笨蛋;而且,本来在生理期我就会比平时更怕冷。
能不能不要装出一副关心我的样子?
真恶心。
我知道,那段时间我的状态看起来糟糕极了。可那跟她有什么关系?让她满意了吗?她是不是还以为,我是因为离了她才变成这样,暗暗得意极了?
但事实上,这根本和她没什么关系。
我只是被压力逼到喘不过气来。
比赛的曲目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确定,因为每一轮都有不同的要求。
第一轮的曲子都已经磨了很久,总算还能拿得出手;而第二轮只能说勉强有了个模样。
最关键的一首奏鸣曲到现在都还悬着;老师希望我冒险,拿最难控制的普罗科菲耶夫参赛。
但我并不喜欢那一首。我始终不理解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对我来说简直难以下咽。
我想选更稳妥、我更喜欢的勃拉姆斯,却被老师否定——她说我的音乐不够深刻,诠释不好勃拉姆斯,展现不出优势。
而我一直以来引以为傲、脱颖而出的扎实技术,才让我更有可能在竞争最激烈的第二轮杀出一条血路。
理性上,我无法反驳这一点;可这确实对我而言是很大的负担。我能感受到,因为过度练习、过度使用,我对手指的控制力和指尖的敏感度正在慢慢流失。
取而代之的是让我夜不能寐的伤痛。
我没有告诉妈妈。
她对我身体上的伤向来嗤之以鼻。起初她还会担心,但带我去看过几次医生,每一次得到的都是“需要休息”这种答案之后,她就失去了耐心。
最后一次,她几乎要在其他患者面前和医生吵起来。她指着医生的鼻子,质问他知不知道我现在处在什么关键阶段——“休息?我女儿现在不可能休息,你知不知道她要代表中国人,参加怎样的比赛?”
因为她的话,周围的人纷纷把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身上。我紧紧攥着手中的单子,尽力让自己不要哭出来。
然而疯狂的母亲还在喋喋不休。
“这一届也就仅仅两个中国人进了正赛——你懂吗,我女儿可能会是第一个拿奖的中国人!”
“我的女儿,她会创造历史!”
——她会创造历史!
———
——————
我已经忘记自己是怎么走出那间人满为患的诊断室的——回想起来,我应该感谢当年的自媒体并没有像10年后一样发达,大家还没有随时拿起手机录像的意识。
妈妈拽着我的胳膊走出医院走廊,我踉跄地被她拖在身后。她恶狠狠地说着,你不要想把这件事当成你不练琴的借口
从现在开始,我不想听到你任何的抱怨。
一切都糟糕极了。
老师可能也跟母亲提了我最近没有什么进步这件事,她开始变本加厉地监视我;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地打电话,甚至会突然过来一个视频,只是为了确认我有没有在练琴。
那天晚上我还在Maggie的房间,妈妈的电话却一通接一通的打过来。
已经是晚上12点多,我刚洗好澡,灯没开,只剩下两个人暧昧的喘吸声。
我正被她抱在怀中,她毛茸茸的卷发贴着我的皮肤,亲吻着我的乳尖。
气氛正正好。
我却有些害羞,因为这几天Abela也在宿舍。
可maggie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想法。
我默默地撇了一眼隔壁床,没有任何动静,她可能已经睡熟了。
Maggie似乎发现了我的不安,她捏住我的下巴,让我强行面对她,给我一个湿热的吻。
我在黑暗中尽力压下呻吟,可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这下叁个人都清醒了。
maggie皱了皱眉头,拿起我的手机自顾自地设成静音。
“别管了。”她咬着我的耳朵,轻声嘟囔着“专心一点。”
“不、我要看……”
我试图推开她的手臂,因为有一股预感告诉我,这就是母亲打来的。
可我被她牢牢固定在怀中。
我叹下一口气,放弃了挣扎,顺从地让她继续。
但在黑暗里,手机的光还是一闪一闪着,那个人还在坚持不懈的给我打着电话。
“我……我可能还是要接一下。”
我推开了她。
她没有说话。
其实我知道她不高兴。
我前几天的生理期,今天好不容易结束了,忍了好几天的她早就问过我,今晚能不能靠近一些。
我也答应了。
可晚上在琴房练得太久,等我回到宿舍时已经很晚了。
而现在,那电话响个不停,简直像催命一样——
我根本没办法假装听不见。
我拿起手机,看到屏幕上的名字,心脏一下子揪紧。
果然,是妈妈。
我匆忙穿好衣服,回到自己的宿舍,才接起电话。
好在房间里就我一个人,许念初大概也去找她的小女友了。
刚接通,迎接我的就是母亲劈头盖脸的质问。
——为什么不接?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委屈的说着自己是去洗澡了。
——洗澡就洗这么久?
我没有回答,只是怔怔地盯着地毯。
——你洗头了吗?
母亲凑近屏幕,试图观察出我的异常。
没有……
——那为什么会这么久!
……..
——你是不是出去跟人鬼混了?!
她突然像是被自己说的话点着,声音也立刻提高了一个八度。
——把衣服脱掉!!!我不信你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那为什么不能马上接我的电话?!
……
听她说完这句话,我其实并不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似乎应该感受到恐惧,或者委屈、羞耻,不安、心虚。
我似乎应该联想到,妈妈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是许念初跟她说了什么吗?
可是我都没有。虚无,空白。
麻木。
我只是抬起头来,直视着手机里的我的妈妈。
她还在喋喋不休着,你不要以为我管不住你,许念安。你别以为你在外面就……
她看上去疲惫又愤怒,正穿着一件不太合身的工作围裙,身后是杂乱的后厨。
我知道,在我们出国之后,她退掉了大城市的房子,回了老家,和爸爸住回一起。
说是一起,其实两人早已没什么感情。我没见到过,他们除去家庭琐事外还有其他什么交流。
为了陪我们念书,她从爸爸的身边,以及从社会消失了太久,已经没法再进入职场,只能在食堂打一份零工。
——她快乐吗?
我曾发到过家里的老相册,里面记录着高中时期的妈妈。有着健康身体的优等生,每次都会报名参加运动会的长跑。
照片里的她站在艳阳下,扎着两条麻花辫,眉眼弯弯地看着镜头,像是坚定地相信自己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我从未真正听过她谈自己的生活。
现在她似乎已经被家庭掏空,一切都围绕着她的女儿。
我应该愧疚吗?
她猜得一点都没错——我确实正和吊儿郎当的Alpha们厮混在一起。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并不愧疚。
我没有脱下衣服给她看,只是装作受了委屈的样子,掉着眼泪诉说自己的不易。
母亲大概对我还抱有一丝怜悯之心,她没有再强求我什么。
挂断电话后,我回到房间,Maggie 还靠在床头玩着手机,我知道,她有些生气了。
我在她身边躺下,从背后抱住她,轻言软语地撒着娇;说是妈妈打来的电话,我不能不接。
她没好气的轻嗤了一声。
——为什么,
她问我。
——我不懂,你为什么不直接挂掉呢?就说你睡觉了。
——我在你这里的优先度就这样低吗?就为了一个电话?
我一时噎住。
这该从何说起呢,她似乎无法理解的东亚母女关系——
如同毒药一般无法抗拒的,无法舍弃的,深入进我的骨血的,对我的绝对控制。
在我人生的前半部分中,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母亲摆布。
不,不、她不是我的母亲。她已经在我未察觉到的时候,变成了我不认识的,
怪物。
后来olivia告诉我的。她看到许念初和那女孩牵手,她们大概是已经在一起了吧。
所以,在我面前不承认有什么用?想瞒着我,又能瞒多久;就我们这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
她们到底从是什么时候开始暧昧的?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一遍遍复盘时间线。那次在食堂,她们是不是就已经开始接触了?所以,这就是她不肯对我说喜欢的原因吗?
因为她其实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渣女。
我甚至开始替那个女孩感到不值得。和这种人谈恋爱到底有什么意思?还不如买一个冬瓜抱着睡,至少它不会说难听的话,不会莫名其妙地作出伤害你的事情。然后,在她开心的时候,又若无其事地靠近你。
明明刚刚还在我面前和自己的女朋友亲亲我我,转头却又毫不避讳地打量着我,凑过来嘘寒问暖;看我一副不想搭理的样子,她就搬出“不是说好在外人面前要和睦相处吗”来要挟我,毫无边界感的对我评头论足。
我当然知道春装在哪里,我不是什么离了她就活不下去的笨蛋;而且,本来在生理期我就会比平时更怕冷。
能不能不要装出一副关心我的样子?
真恶心。
我知道,那段时间我的状态看起来糟糕极了。可那跟她有什么关系?让她满意了吗?她是不是还以为,我是因为离了她才变成这样,暗暗得意极了?
但事实上,这根本和她没什么关系。
我只是被压力逼到喘不过气来。
比赛的曲目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确定,因为每一轮都有不同的要求。
第一轮的曲子都已经磨了很久,总算还能拿得出手;而第二轮只能说勉强有了个模样。
最关键的一首奏鸣曲到现在都还悬着;老师希望我冒险,拿最难控制的普罗科菲耶夫参赛。
但我并不喜欢那一首。我始终不理解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对我来说简直难以下咽。
我想选更稳妥、我更喜欢的勃拉姆斯,却被老师否定——她说我的音乐不够深刻,诠释不好勃拉姆斯,展现不出优势。
而我一直以来引以为傲、脱颖而出的扎实技术,才让我更有可能在竞争最激烈的第二轮杀出一条血路。
理性上,我无法反驳这一点;可这确实对我而言是很大的负担。我能感受到,因为过度练习、过度使用,我对手指的控制力和指尖的敏感度正在慢慢流失。
取而代之的是让我夜不能寐的伤痛。
我没有告诉妈妈。
她对我身体上的伤向来嗤之以鼻。起初她还会担心,但带我去看过几次医生,每一次得到的都是“需要休息”这种答案之后,她就失去了耐心。
最后一次,她几乎要在其他患者面前和医生吵起来。她指着医生的鼻子,质问他知不知道我现在处在什么关键阶段——“休息?我女儿现在不可能休息,你知不知道她要代表中国人,参加怎样的比赛?”
因为她的话,周围的人纷纷把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身上。我紧紧攥着手中的单子,尽力让自己不要哭出来。
然而疯狂的母亲还在喋喋不休。
“这一届也就仅仅两个中国人进了正赛——你懂吗,我女儿可能会是第一个拿奖的中国人!”
“我的女儿,她会创造历史!”
——她会创造历史!
———
——————
我已经忘记自己是怎么走出那间人满为患的诊断室的——回想起来,我应该感谢当年的自媒体并没有像10年后一样发达,大家还没有随时拿起手机录像的意识。
妈妈拽着我的胳膊走出医院走廊,我踉跄地被她拖在身后。她恶狠狠地说着,你不要想把这件事当成你不练琴的借口
从现在开始,我不想听到你任何的抱怨。
一切都糟糕极了。
老师可能也跟母亲提了我最近没有什么进步这件事,她开始变本加厉地监视我;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地打电话,甚至会突然过来一个视频,只是为了确认我有没有在练琴。
那天晚上我还在Maggie的房间,妈妈的电话却一通接一通的打过来。
已经是晚上12点多,我刚洗好澡,灯没开,只剩下两个人暧昧的喘吸声。
我正被她抱在怀中,她毛茸茸的卷发贴着我的皮肤,亲吻着我的乳尖。
气氛正正好。
我却有些害羞,因为这几天Abela也在宿舍。
可maggie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想法。
我默默地撇了一眼隔壁床,没有任何动静,她可能已经睡熟了。
Maggie似乎发现了我的不安,她捏住我的下巴,让我强行面对她,给我一个湿热的吻。
我在黑暗中尽力压下呻吟,可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这下叁个人都清醒了。
maggie皱了皱眉头,拿起我的手机自顾自地设成静音。
“别管了。”她咬着我的耳朵,轻声嘟囔着“专心一点。”
“不、我要看……”
我试图推开她的手臂,因为有一股预感告诉我,这就是母亲打来的。
可我被她牢牢固定在怀中。
我叹下一口气,放弃了挣扎,顺从地让她继续。
但在黑暗里,手机的光还是一闪一闪着,那个人还在坚持不懈的给我打着电话。
“我……我可能还是要接一下。”
我推开了她。
她没有说话。
其实我知道她不高兴。
我前几天的生理期,今天好不容易结束了,忍了好几天的她早就问过我,今晚能不能靠近一些。
我也答应了。
可晚上在琴房练得太久,等我回到宿舍时已经很晚了。
而现在,那电话响个不停,简直像催命一样——
我根本没办法假装听不见。
我拿起手机,看到屏幕上的名字,心脏一下子揪紧。
果然,是妈妈。
我匆忙穿好衣服,回到自己的宿舍,才接起电话。
好在房间里就我一个人,许念初大概也去找她的小女友了。
刚接通,迎接我的就是母亲劈头盖脸的质问。
——为什么不接?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委屈的说着自己是去洗澡了。
——洗澡就洗这么久?
我没有回答,只是怔怔地盯着地毯。
——你洗头了吗?
母亲凑近屏幕,试图观察出我的异常。
没有……
——那为什么会这么久!
……..
——你是不是出去跟人鬼混了?!
她突然像是被自己说的话点着,声音也立刻提高了一个八度。
——把衣服脱掉!!!我不信你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那为什么不能马上接我的电话?!
……
听她说完这句话,我其实并不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似乎应该感受到恐惧,或者委屈、羞耻,不安、心虚。
我似乎应该联想到,妈妈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是许念初跟她说了什么吗?
可是我都没有。虚无,空白。
麻木。
我只是抬起头来,直视着手机里的我的妈妈。
她还在喋喋不休着,你不要以为我管不住你,许念安。你别以为你在外面就……
她看上去疲惫又愤怒,正穿着一件不太合身的工作围裙,身后是杂乱的后厨。
我知道,在我们出国之后,她退掉了大城市的房子,回了老家,和爸爸住回一起。
说是一起,其实两人早已没什么感情。我没见到过,他们除去家庭琐事外还有其他什么交流。
为了陪我们念书,她从爸爸的身边,以及从社会消失了太久,已经没法再进入职场,只能在食堂打一份零工。
——她快乐吗?
我曾发到过家里的老相册,里面记录着高中时期的妈妈。有着健康身体的优等生,每次都会报名参加运动会的长跑。
照片里的她站在艳阳下,扎着两条麻花辫,眉眼弯弯地看着镜头,像是坚定地相信自己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我从未真正听过她谈自己的生活。
现在她似乎已经被家庭掏空,一切都围绕着她的女儿。
我应该愧疚吗?
她猜得一点都没错——我确实正和吊儿郎当的Alpha们厮混在一起。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并不愧疚。
我没有脱下衣服给她看,只是装作受了委屈的样子,掉着眼泪诉说自己的不易。
母亲大概对我还抱有一丝怜悯之心,她没有再强求我什么。
挂断电话后,我回到房间,Maggie 还靠在床头玩着手机,我知道,她有些生气了。
我在她身边躺下,从背后抱住她,轻言软语地撒着娇;说是妈妈打来的电话,我不能不接。
她没好气的轻嗤了一声。
——为什么,
她问我。
——我不懂,你为什么不直接挂掉呢?就说你睡觉了。
——我在你这里的优先度就这样低吗?就为了一个电话?
我一时噎住。
这该从何说起呢,她似乎无法理解的东亚母女关系——
如同毒药一般无法抗拒的,无法舍弃的,深入进我的骨血的,对我的绝对控制。
在我人生的前半部分中,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母亲摆布。
不,不、她不是我的母亲。她已经在我未察觉到的时候,变成了我不认识的,
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