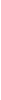琉璃心里一阵难受,伸手环住了他的腰:胡说!你哪里是自作聪明,你是思虑得太周全,也太过求全责备。你不用担心,义母jīng神好多了,适才十三娘还特意过来劝慰了阿母,阿母都听进去了。
她把十三娘的话转述了一遍后说:她说得原是不错,无论此时如何,千秋之后,义父照样是一代名将,这一时的得失荣rǔ又算什么?若如此冷遇,真是宰相们的缘故,他们自然该承担后果。难不成任由他们装聋作哑,令圣人耳目蔽塞,才算对得起朝廷?守约,你总说,世事难料,有时不能去想利弊,只能求个问心无愧,怎么事到临头,还是这样为难你自己?
裴行俭沉默片刻,苦笑着点点头:你说得是。无论那几位相公为何如此,无论结果如何,他们敢做便该敢当!过犹不及,是我着相了!
他抬头凝视着挂在墙上的那些长弓短剑,久久地没有出声。琉璃也转头看了过去,这些兵器大概都是苏定方用过的,刀柄弓背上犹自泛着常年摩挲留下的沉稳光泽,大概再过多少年也不会褪色。
裴行俭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人心易变,世事无常,唯有功业,能历百世而不朽。恩师他,定然可以流芳千载!他转身走到案几前跪坐下来,展开纸卷,提笔一了下去。
烛光下,那一行行端凝的墨书也闪动着同样沉稳的光泽,仿佛不会被世间的任何东西磨灭。
两日之后,这份奏章才终于出现在紫宸殿书房的案头。
李治原是有些倦意,只是撑着额头读了两行,便腾地坐直了身子,待到字字读完,更是霍然而起,拂袖一甩。就听啪的声脆响,案几上那方白玉瑞shòu镇纸与雕着莲花纹的地砖顷刻间已是两败俱伤。
一旁服侍的窦宽唬了一大跳,等了半晌,见皇帝没有别的动静,才悄悄上前将那已缺了一角的镇纸捡了起来。他还未直起腰,就听书案后李治突然笑出了声:这便是大唐的宰相们,这便是朕的宰相们!
这笑声冷峭入骨,窦宽身子一僵,忙弯腰退后了好几步,抬头一瞟,却见李治一不动地站在书案后,咬牙瞪着门外,只是看着看着,脸上的嘲讽和怒色,却渐渐变成了一片惘然,眼角的皱纹看上去都深了几分。
良久之后,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也变得有些沙哑:传朕的旨意,让几位相公即刻进殿!
没过多久,这沙哑的声音便回dàng在大唐最有权势的几位朝臣耳边:苏定方于国有功,按礼应予褒赠,你们为何一字不提!
一片沉默中,紫宸殿的空气似乎变得越来越黏稠沉重,终于凝聚成bào雨前的乌云。
次日一封迟来的诏书终于抵达苏府,追赠苏定方为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苏庆节按例减等袭爵为章武郡公。
六日后,朝廷终于议定苏定方谥号为庄;同日,被擢为宰相不到半年的东台侍郎李安期悄然离开长安。让他出任荆州长史的诏书写得四平八稳,可所有的人都分明地感受到了皇帝那不动声色的怒火与警告。
十天后,朝廷迎来了更大的地震:皇帝李治因久病难愈,沼令太子李弘监国。
一时间,少阳院内外一片阳光明媚,含凉殿上空多少有些yīn晴不定,至于长安城的各大宫宅府衙里,更是不知几处chūn风得意,几处秋雨飘摇。
不过,对于早巳闭门谢客的苏府来说,这样的消息巳是激不起任何波澜。琉璃也只是在心里冷笑了一声这位多愁多病的皇帝是在发现舅舅靠不住,老婆靠不住,自己一手提拔的宰相们也靠不住之后,只好准备靠儿子来帮他治理天下了吗?他还真是她摇了摇头,把所有的思绪都抛到了一边。九月的阳光从树叶间洒落下来,将她身上的本白色粗麻裙染上了斑斑点点的暖色,仿佛是洒下了一朵朵细碎的jú花。
院子里,金huáng的jú花开得正好,将空dàngdàng的庭院映衬得秋意盎然。微风chuī过,那些素色的灯笼和颜色渐渐绚烂起来的树叶一道发出了飒飒的轻响。
不远处一棵枝叶茂密的枫树下,rǔ娘正抱着三郎去够刚刚泛红的树叶,三郎努力了几回,终于一把抓下了半片叶子,高兴得蹬着腿大笑:啊呀!啊呀!
坐在一旁的于夫人与罗氏都笑出了声:这孩子,倒是会惦记人的!
琉璃也笑了起来,目光却不由看向了西边,那边的天际没有一丝云彩,只有两行大雁,在碧色天幕上写下了一个略显凌乱的人字。三郎的那位阿爷,如今已在数百里之外了吧?皇帝驳回了他辞官的请求,却令他以司文少卿的身份出京协理故邢国公归葬事宜。七天前,她在开远门外目送着他再次踏上漫漫丝路,那是通往西州的路,也是五年前苏定方离开长安时走过的路。但有些路,无论如何,她都不想看见他再走一遍不知此时此刻,他头上的天空,是否也如此晴好?
第十章相由心生祸从耳入
又是一年早chūn时节。
经过那风波迭起的秋日和一个漫长沉闷的寒冬之后,长安人对于这个chūn天似乎格外期待。随着二月的东风渐次chuī开百花,休养了好几个月的天子终于重新出现在朝堂之上,雄心勃勃地着手制定明堂制度,加上高丽战场上节节胜利的喜讯不断传来,整个长安城都陷入了一种狂欢的氛围,新酒酿成的浓香、踏花归来的清香和着响亮的欢声笑语,飘dàng在城坊的每个角落。
自然也有例外。
休祥坊荣国夫人府里的西院,重门深掩,满地青苔,几棵高大的梨树不久前还是繁花满枝,此时那细碎的白色花瓣却已飘飘洒洒落了满院,仿佛一地将融未融的残雪。huáng昏的余晖从西边的阁楼上照了进来,竟似带着股深冬的气息。
一片寂静之中,上房门突然发出了剌耳的吱呀一声。有人摔帘而出,脚步带风地走下台阶,白袍飘飞,惊起了一路落花。一位丰硕的身影随即追了出来:小郎君留步!小郎君留步!
白袍一顿,恰恰停在了一棵梨树下。
武敏之狠狠地吐了口气,沉着脸转过身来,认得追过来的正是这两年武夫人身边最得力的管事娘子,眼神更冷了三分。
饶是阿霓早已受惯了这样的目光,脚步还是下意识的一缓,小心翼翼地低声道:小郎君,您先消消气,您也知道,夫人自打入冬,身子便有些虚,如今当真是不能再添忧思的。此次夫人要做法事,也是她的一片慈心,您若是觉得不妥,慢慢劝说夫人便是,如此盛怒而去,岂不是让夫人心里更过不得?再说此次的法事,老夫人那边
武敏之神色不变,只是慢慢抬高了下颌,看着她一言不发。阿霓的声音不由自主越来越低,终于讷讷的再也说不下去。他这才挑了挑眉,语气清淡得听不出半点嘲讽:夫人身子既然不好,就该在家中好好休养,不用这样隔三岔五地提醒旁人,她有多惦记着月娘!
还有你们,服侍好夫人,让她少出门进宫的折腾自己是正经。你们年岁也不小了,没那么多富贵前程在那里等着你们,还是消停些吧!
这话一句句的实在太过诛心,阿霓的脸上一阵发烫一阵冰凉,一时竟不知如何分解。沉默间,背后的上房又传来了一阵隐隐的咳嗽声,纵然隔着门窗,也听得出那种撕裂般的不祥意味。武敏之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眯着眼看了上房一眼,掉头就走。
阿霓再也忍耐不住,哑声道:小郎君,夫人已是这样了,您真忍心让夫人就这两年也过不去么?
武敏之霍然转身,目光冰冷锐利有如霜刃:你说什么?什么这两年?
阿霓唬了一跳,想往后退,脚下却有点拌蒜。她还没站稳,武敏之已bī上两步,面孔竟似带上一层淡淡的青色:是谁跟你说的这种混账话!
阿霓差点结巴起来:小、小郎君不是从老夫人那边过来的么?是前些日子明先生给夫人看诊之后说,夫人久郁之下,这一病巳是伤了元气,只怕、只怕总之是万万不能再郁结于中的。老夫人没跟您说?
武成敏之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阵东风chuī过,枝头的花瓣窣窣洒落,好几朵落在在他洁白如雪的衣襟上,仿佛溅上了微huáng的泪渍。他的眸子终于转了转,突然冷笑了一声:明崇俨?他算什么东西!难不成从这里骗到的诊金还不够多,要如此危言耸听才好显示他的手段!
阿霓神色微黯,低声回道:老夫人也是不肯信,因此前两日特意将张真人来给夫人看过一遍,说法虽不尽相似,却也差不太多。张真人还说,夫人的病不是药石能及的,让我们凡事都顺着她些,若是能解开心头郁结,比什么灵丹妙药都qiáng。夫人自己也猜出了几分,因此今年才一定要自己去寺院施斋,说是如今能做一点就是一点,以后只怕就是想做也不成了。
武敏之脸上神qíng未变,眸子里却愈发黑沉沉的没有一丝光亮:既然如此,老夫人怎么肯让她去那么远的地方?
老夫人原本也是不赞同的,只是夫人执意如此,老夫人也没法子,因此才特意选了终南山的信行禅师塔寺。那里风光最好,边上又有极清静的尼寺。老夫人还将平日里与夫人jiāo好的几位夫人娘子都请了同去,小郎君若肯过去主持布施,夫人这趟出去倒是正好散散心,阿霓小心地看了看武敏之的脸色,小郎君,您若是实在不放心,不如回去跟夫人好好说一说?
武敏之的目光不知落在什么地方,沉默良久,才缓缓摇了摇头:不必了。你跟夫人回报一声,说我明白了,让夫人这几日好好休养,我
阿霓心头一松,忙应了声诺,抬头等着他的下文。武敏之却转头看着上房,久久没有开口。斜阳将树影斑驳地洒在他的身上,他的脸色看去一片雪白,连唇上似乎都没有血色,眉眼却愈发深黑。阿霓突然有些不敢呼吸,在落英缤纷的chūn日huáng昏里,眼前的这张面孔有一种开到极致的光华,仿佛只要chuī上一口气,就会如满树残花般在风中凋零。
不知过了多久,武敏之低低的声音才响了起来:我会陪夫人过去!他转身走出了院子,院门微合,掩住了那个清冷的身影。
荣国夫人府的正院与西院相隔得并不远,武敏之却足足走了一炷香的时间才到。守在院门口的两个小婢女瞧见他的身影,一个忙忙地转身进去回报,另一个便上来笑道:小郎君怎么才过来?老夫人问了两回了。
--
她把十三娘的话转述了一遍后说:她说得原是不错,无论此时如何,千秋之后,义父照样是一代名将,这一时的得失荣rǔ又算什么?若如此冷遇,真是宰相们的缘故,他们自然该承担后果。难不成任由他们装聋作哑,令圣人耳目蔽塞,才算对得起朝廷?守约,你总说,世事难料,有时不能去想利弊,只能求个问心无愧,怎么事到临头,还是这样为难你自己?
裴行俭沉默片刻,苦笑着点点头:你说得是。无论那几位相公为何如此,无论结果如何,他们敢做便该敢当!过犹不及,是我着相了!
他抬头凝视着挂在墙上的那些长弓短剑,久久地没有出声。琉璃也转头看了过去,这些兵器大概都是苏定方用过的,刀柄弓背上犹自泛着常年摩挲留下的沉稳光泽,大概再过多少年也不会褪色。
裴行俭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人心易变,世事无常,唯有功业,能历百世而不朽。恩师他,定然可以流芳千载!他转身走到案几前跪坐下来,展开纸卷,提笔一了下去。
烛光下,那一行行端凝的墨书也闪动着同样沉稳的光泽,仿佛不会被世间的任何东西磨灭。
两日之后,这份奏章才终于出现在紫宸殿书房的案头。
李治原是有些倦意,只是撑着额头读了两行,便腾地坐直了身子,待到字字读完,更是霍然而起,拂袖一甩。就听啪的声脆响,案几上那方白玉瑞shòu镇纸与雕着莲花纹的地砖顷刻间已是两败俱伤。
一旁服侍的窦宽唬了一大跳,等了半晌,见皇帝没有别的动静,才悄悄上前将那已缺了一角的镇纸捡了起来。他还未直起腰,就听书案后李治突然笑出了声:这便是大唐的宰相们,这便是朕的宰相们!
这笑声冷峭入骨,窦宽身子一僵,忙弯腰退后了好几步,抬头一瞟,却见李治一不动地站在书案后,咬牙瞪着门外,只是看着看着,脸上的嘲讽和怒色,却渐渐变成了一片惘然,眼角的皱纹看上去都深了几分。
良久之后,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也变得有些沙哑:传朕的旨意,让几位相公即刻进殿!
没过多久,这沙哑的声音便回dàng在大唐最有权势的几位朝臣耳边:苏定方于国有功,按礼应予褒赠,你们为何一字不提!
一片沉默中,紫宸殿的空气似乎变得越来越黏稠沉重,终于凝聚成bào雨前的乌云。
次日一封迟来的诏书终于抵达苏府,追赠苏定方为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苏庆节按例减等袭爵为章武郡公。
六日后,朝廷终于议定苏定方谥号为庄;同日,被擢为宰相不到半年的东台侍郎李安期悄然离开长安。让他出任荆州长史的诏书写得四平八稳,可所有的人都分明地感受到了皇帝那不动声色的怒火与警告。
十天后,朝廷迎来了更大的地震:皇帝李治因久病难愈,沼令太子李弘监国。
一时间,少阳院内外一片阳光明媚,含凉殿上空多少有些yīn晴不定,至于长安城的各大宫宅府衙里,更是不知几处chūn风得意,几处秋雨飘摇。
不过,对于早巳闭门谢客的苏府来说,这样的消息巳是激不起任何波澜。琉璃也只是在心里冷笑了一声这位多愁多病的皇帝是在发现舅舅靠不住,老婆靠不住,自己一手提拔的宰相们也靠不住之后,只好准备靠儿子来帮他治理天下了吗?他还真是她摇了摇头,把所有的思绪都抛到了一边。九月的阳光从树叶间洒落下来,将她身上的本白色粗麻裙染上了斑斑点点的暖色,仿佛是洒下了一朵朵细碎的jú花。
院子里,金huáng的jú花开得正好,将空dàngdàng的庭院映衬得秋意盎然。微风chuī过,那些素色的灯笼和颜色渐渐绚烂起来的树叶一道发出了飒飒的轻响。
不远处一棵枝叶茂密的枫树下,rǔ娘正抱着三郎去够刚刚泛红的树叶,三郎努力了几回,终于一把抓下了半片叶子,高兴得蹬着腿大笑:啊呀!啊呀!
坐在一旁的于夫人与罗氏都笑出了声:这孩子,倒是会惦记人的!
琉璃也笑了起来,目光却不由看向了西边,那边的天际没有一丝云彩,只有两行大雁,在碧色天幕上写下了一个略显凌乱的人字。三郎的那位阿爷,如今已在数百里之外了吧?皇帝驳回了他辞官的请求,却令他以司文少卿的身份出京协理故邢国公归葬事宜。七天前,她在开远门外目送着他再次踏上漫漫丝路,那是通往西州的路,也是五年前苏定方离开长安时走过的路。但有些路,无论如何,她都不想看见他再走一遍不知此时此刻,他头上的天空,是否也如此晴好?
第十章相由心生祸从耳入
又是一年早chūn时节。
经过那风波迭起的秋日和一个漫长沉闷的寒冬之后,长安人对于这个chūn天似乎格外期待。随着二月的东风渐次chuī开百花,休养了好几个月的天子终于重新出现在朝堂之上,雄心勃勃地着手制定明堂制度,加上高丽战场上节节胜利的喜讯不断传来,整个长安城都陷入了一种狂欢的氛围,新酒酿成的浓香、踏花归来的清香和着响亮的欢声笑语,飘dàng在城坊的每个角落。
自然也有例外。
休祥坊荣国夫人府里的西院,重门深掩,满地青苔,几棵高大的梨树不久前还是繁花满枝,此时那细碎的白色花瓣却已飘飘洒洒落了满院,仿佛一地将融未融的残雪。huáng昏的余晖从西边的阁楼上照了进来,竟似带着股深冬的气息。
一片寂静之中,上房门突然发出了剌耳的吱呀一声。有人摔帘而出,脚步带风地走下台阶,白袍飘飞,惊起了一路落花。一位丰硕的身影随即追了出来:小郎君留步!小郎君留步!
白袍一顿,恰恰停在了一棵梨树下。
武敏之狠狠地吐了口气,沉着脸转过身来,认得追过来的正是这两年武夫人身边最得力的管事娘子,眼神更冷了三分。
饶是阿霓早已受惯了这样的目光,脚步还是下意识的一缓,小心翼翼地低声道:小郎君,您先消消气,您也知道,夫人自打入冬,身子便有些虚,如今当真是不能再添忧思的。此次夫人要做法事,也是她的一片慈心,您若是觉得不妥,慢慢劝说夫人便是,如此盛怒而去,岂不是让夫人心里更过不得?再说此次的法事,老夫人那边
武敏之神色不变,只是慢慢抬高了下颌,看着她一言不发。阿霓的声音不由自主越来越低,终于讷讷的再也说不下去。他这才挑了挑眉,语气清淡得听不出半点嘲讽:夫人身子既然不好,就该在家中好好休养,不用这样隔三岔五地提醒旁人,她有多惦记着月娘!
还有你们,服侍好夫人,让她少出门进宫的折腾自己是正经。你们年岁也不小了,没那么多富贵前程在那里等着你们,还是消停些吧!
这话一句句的实在太过诛心,阿霓的脸上一阵发烫一阵冰凉,一时竟不知如何分解。沉默间,背后的上房又传来了一阵隐隐的咳嗽声,纵然隔着门窗,也听得出那种撕裂般的不祥意味。武敏之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眯着眼看了上房一眼,掉头就走。
阿霓再也忍耐不住,哑声道:小郎君,夫人已是这样了,您真忍心让夫人就这两年也过不去么?
武敏之霍然转身,目光冰冷锐利有如霜刃:你说什么?什么这两年?
阿霓唬了一跳,想往后退,脚下却有点拌蒜。她还没站稳,武敏之已bī上两步,面孔竟似带上一层淡淡的青色:是谁跟你说的这种混账话!
阿霓差点结巴起来:小、小郎君不是从老夫人那边过来的么?是前些日子明先生给夫人看诊之后说,夫人久郁之下,这一病巳是伤了元气,只怕、只怕总之是万万不能再郁结于中的。老夫人没跟您说?
武成敏之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阵东风chuī过,枝头的花瓣窣窣洒落,好几朵落在在他洁白如雪的衣襟上,仿佛溅上了微huáng的泪渍。他的眸子终于转了转,突然冷笑了一声:明崇俨?他算什么东西!难不成从这里骗到的诊金还不够多,要如此危言耸听才好显示他的手段!
阿霓神色微黯,低声回道:老夫人也是不肯信,因此前两日特意将张真人来给夫人看过一遍,说法虽不尽相似,却也差不太多。张真人还说,夫人的病不是药石能及的,让我们凡事都顺着她些,若是能解开心头郁结,比什么灵丹妙药都qiáng。夫人自己也猜出了几分,因此今年才一定要自己去寺院施斋,说是如今能做一点就是一点,以后只怕就是想做也不成了。
武敏之脸上神qíng未变,眸子里却愈发黑沉沉的没有一丝光亮:既然如此,老夫人怎么肯让她去那么远的地方?
老夫人原本也是不赞同的,只是夫人执意如此,老夫人也没法子,因此才特意选了终南山的信行禅师塔寺。那里风光最好,边上又有极清静的尼寺。老夫人还将平日里与夫人jiāo好的几位夫人娘子都请了同去,小郎君若肯过去主持布施,夫人这趟出去倒是正好散散心,阿霓小心地看了看武敏之的脸色,小郎君,您若是实在不放心,不如回去跟夫人好好说一说?
武敏之的目光不知落在什么地方,沉默良久,才缓缓摇了摇头:不必了。你跟夫人回报一声,说我明白了,让夫人这几日好好休养,我
阿霓心头一松,忙应了声诺,抬头等着他的下文。武敏之却转头看着上房,久久没有开口。斜阳将树影斑驳地洒在他的身上,他的脸色看去一片雪白,连唇上似乎都没有血色,眉眼却愈发深黑。阿霓突然有些不敢呼吸,在落英缤纷的chūn日huáng昏里,眼前的这张面孔有一种开到极致的光华,仿佛只要chuī上一口气,就会如满树残花般在风中凋零。
不知过了多久,武敏之低低的声音才响了起来:我会陪夫人过去!他转身走出了院子,院门微合,掩住了那个清冷的身影。
荣国夫人府的正院与西院相隔得并不远,武敏之却足足走了一炷香的时间才到。守在院门口的两个小婢女瞧见他的身影,一个忙忙地转身进去回报,另一个便上来笑道:小郎君怎么才过来?老夫人问了两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