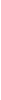裴行俭沉声道,放他起来,不许他乱动!
差役们闻言才松了手,只留下两人站在孔大郎的左右。孔大郎抹了抹脸上的尘土,依然恨恨的看着义照,只是到底不敢再扑过去。姜氏和令氏此时一个比一个哭得厉害。裴行俭却默然看着下面的乱象,也不知在想什么。
麴崇裕走上一步,淡淡的笑道,这案子真真越发有趣了,不知裴长史该如何了断?
裴行俭摇了摇头,有悖人伦,莫过于此,何趣之有?扬声道,令氏,你有何可说?
令氏慢慢止住了哭泣,伏地回道,启禀裴长史,小妇人的儿媳姜氏不守妇德,生xingbào躁,时常rǔ骂于我,又污蔑高僧,今日小妇人是忍无可忍,才告发了这恶媳。小妇人的儿子好吃懒做,对小妇人无甚奉养,又纵容儿媳无礼,望长史为小妇人做主。声音略有些颤抖,却愈发显得悲凉。
孔大郎呆了一下,似乎万万没料到母亲不但没松口,反而添上了自己,高声叫了一句,阿娘!嗓音已全然变音。姜氏也瞪大眼睛看着令氏,不知是愤怒还是害怕,全身都在发抖。
都护府外诸人有xing急的便呸了一声,这孔大郎为护着自己妻子竟能向僧人动手,可见平日定然也不是个孝顺的!
裴行俭语气沉肃,令氏,你是要告儿媳忤逆,儿子奉养不周?你可知忤逆乃是死罪,奉养不周要徒三年?
麴崇裕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嗤笑,别的罪状也罢了,这忤逆不孝要入罪,便是村夫村妇也人人知晓的,他裴行俭还想拦着人告状不成?
令氏脸色发白,沉默半晌,颤声道,小妇人着实是活不下去日后便是自己下地做活挣命,也胜过这般苦熬!请长史做主!说着伏地痛哭。
裴行俭看向姜氏,姜氏,你还未问完,姜氏突然眼睛一翻,身子一软,昏了过去。
孔大郎并没有看姜氏,只张大嘴看着母亲,突然叫道,母亲,你真是要阿姜死么?你真要儿子流放三年?你
令氏猛的抬起头来,盯着他,你便这般不容我活下去?事到如今,还是要忤逆于我么!
孔大郎顿时说不出话来,脸色渐渐变得一片灰白。
裴行俭皱眉半响,叹了口气,来人,把孔大郎和姜氏收押,好生看管。
麴崇裕在一边看着他的脸色,嘴角眉梢都扬得高了几分,转头问对朱阙此案如此明白,裴长史为何不当堂判决?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身边数人听见。
裴行俭恍若无闻,声音平静的对下面的令氏道,令氏,本官会秉公办理此案,你们一家原是外迁之户,并无亲族,姜氏忤逆,论律当绞,而孔大郎要徒三年,姜氏无人收尸,你今日回去便准备一口棺木,明日棺木运到,本官便判决。你这便下去准备吧!
朱阙点了点头,低声对麴崇裕道,还是长史考虑周全。麴崇裕心qíng甚好,笑了笑也未做声。
令氏磕头谢恩,抹着眼泪往外而去,门外看热闹之人,都自觉的闪出一条道来,不少人还同qíng的叹息了几声,裴行俭的目光落在她的背影上,神色里一片漠然。
大佛寺的寺主法谦法师上前一步,合十行礼,长史,孔家家门出此不幸,令檀越孤苦无依,大佛寺不愿再追究欠租,愿撤销诉状。
裴行俭点头一笑,多谢大师体恤。只是此事既由贵寺诉状而起,明日还请义照大僧来做个见证,有劳了。
法谦微一犹豫,点了点头,与脸色好容易回转红润的义照一同告退而去。人群再次闪开极宽的一条路,不少人都神色恭敬的低头行礼。又见都护府里差役已经开始收拾院子,这才jiāo头接耳的慢慢散去。
麴崇裕收回目光,神色愈发愉悦,挑眉看了看从案几后站起身来的裴行俭,长史这案断得gān净利落,与以前大不相同。那件jī毛蒜皮的案子他生生拖了两日,这件忤逆大案他却是断得痛快!不过再快却也挡不住此事流传了。
裴行俭本来略有些出神,听了这话,倒是笑了起来,此案原本极是明白,又无证人可询,自与他案不能相提并论。又温言笑道,不知世子今夜可是有暇?
麴崇裕微微一愣,长史有事?
裴行俭点了点头,下官得了一壶好酒,只是喝的时辰地方都会有特别的讲究,世子若是有暇,正想邀世子同饮。
麴崇裕长长的喔了一声,看着裴行俭,凤目微眯,眼神深邃,守约还有此等雅兴?我一定奉陪!
时近五月,西州的白日已变得颇为漫长,好容易天色才彻底黑下来。残月还未升起,漫天的星斗却分外明亮。星光照在离西州不过十余里地的山壁上,让那些黑漆漆的窑dòng便如一只只黑色的眸子,似乎都在默默注视着山脚下那处并不明亮的灯火。
在一处离地面一丈多高的窑dòng里,黑暗寂静之中,却隐隐有一缕酒香飘dàng。裴行俭和麴崇裕都坐在窑dòng口上,一人手里拿着一个酒囊,借着外面的星光,不时喝上一口。
麴崇裕的玉狮子和裴行俭的坐骑早已被随行的府兵远远的带到了山后,带的酒囊也已经空了大半,麴崇裕终于不耐烦的叹了口气,裴长史,你这酒自然是好的,不过恕崇裕迟钝,你选的地方时辰,我却看不出妙处来。
他的身上穿了一件披风,只是这野外的夜风一chuī,那凉意似乎依然可以直入骨髓半夜三更来这种鬼地方喝酒,他真是疯了才会相信裴行俭的话!
裴行俭声音笃定,世子莫急,在此喝酒,与众不同之处转眼便知。
麴崇裕冷冷道,裴长史果然风雅,就夜风喝冷酒,也能悠然自得,崇裕佩服得紧。而且大路不走,偏要偏鬼鬼祟祟的走小道,进了这窑dòng,又是一坐半天,火褶都不让点,说是特意来喝酒,简直是见鬼,说是做贼倒是差不多。可这地方除了一片果园,几处菜园,一户人家以及无数荒废的窑dòng外,什么都没有,难不成他们是来偷瓜的?
在窑dòng外照进来的微弱星光中,裴行俭突然身子一动,指向一处地方,来了!
麴崇裕诧异的转头看了过去,只见那户人家的大门一看,屋里的灯光倾泻了出来,随即门又合上,有马灯的光线一晃一晃的向这边山壁而来。麴崇裕不由直起了身子,难不成裴行俭约了人半夜在窑dòng相见?
只见裴行俭果然站了起来,世子请跟我来。一口饮尽酒囊里的残酒,丢下酒囊,轻巧的跳了下去。
麴崇裕在进这窑dòng时便知,这位外貌儒雅的裴长史居然颇有身手,此时也不甘示弱,翻身跳落岩下。
裴行俭压低了声音,咱们过去,莫惊动了他们。
麴崇裕心头一动,念头急转,突然有几分明白过来,猛地收住了脚步,裴长史,你带我过来,可是发现今日的案子有古怪之处?
裴行俭回头看向他,果然瞒不了世子,不如世子稍候片刻,让下官过去看看便回?
麴崇裕一声冷笑,知道裴行俭这句话是以退为进,可心里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涌了上来,默然片刻还是淡淡的道,既然来了,一同过去便是。
窑dòng下的小路似乎已多年无人走动,只是对于这两人来说,却不是问题,两人沿着山壁一路往下,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响动。那晃动的马灯不久便接近了山崖最靠下面一处窑dòng,在窑dòng的灯光中无声无息的熄灭。
麴崇裕此时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成,想到白天的一幕,只觉得胸口一团怒火腾的烧了起来。
眼见离山壁上唯一有灯光的那处窑dòng只有十几步远,裴行俭回身打了个手势,两人脚步愈轻,悄然接近了窑dòng的窗口。
只听女子的抽泣之声从窗子里隐隐传了出来,又有男子的声音道,好了,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只是今日你也看见,你既然告了姜氏忤逆,你家大郎虽然孝顺你,却是要跟我拼命的。
那女声顿了一顿,才泣道,若不是看出这一点,你当我忍心叫他流放三年?那是我怀胎十月养下的儿子,如今看我便像仇人一般都是为了你这冤孽!
那男子叹了口气,心肝儿,我知晓你的难处,日后定会好好待你,我回头便跟上座禀告你孤苦可怜,没有这些田地租种,只怕活不下去,上座定然会允许你续租下去,说不定还会减些租子。咱们就在这里守着田地,一个外人没有,再不用似以前般偷偷摸摸,岂不是神仙般的日子?顿了顿又道,你也不早些跟我说,那姜氏,你告个不孝也就罢了,何必要说忤逆?
女声顿时锐利起来,怎么,你舍不得?你当我不知晓你打的什么主意?你哪日里不寻机跟那骚蹄子说几句,她一见你便脸红,都当我是瞎子么?这还没上手的,自然是分外惦记些,你若不甘心,去官府告了我便是,咱们两条命换她一条如何,你她越说声音越高,突然呜呜两声,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片刻之后,那男声才重新响了起来,你说什么昏话?一不做二不休,到了如今的田地,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今日连城里都不住要过来,便是要告诉你,明日无论怎样,你都不能心软。便是大郎嚷出咱们的事qíng,你也一口咬定他是为了救自家媳妇污蔑于你!
女声带点迟疑,若是那样大郎会不会
男声狠狠的道,诬告父母,自是恶逆的死罪,大郎今日还算识相,我只怕他明日见姜氏要被绞杀,昏了头,什么话都会往外倒,你却绝不能心软,不但不能松口,连神色都不能露一点风出来,那裴长史听说是个极厉害的,今日他是后头才赶到,不然你我只怕还不会如此顺遂。
女声停了半晌,带上了哭音,可是大郎
男人道,我也不愿如此,只是事到如今,你若舍不得他死,那便是咱们永世不能在一起,你可舍得?如今只要打发了那两个,咱们便是活神仙一般说着说着,里面的动静变得古怪起来,那女子的哭音也渐渐变成了喘息,隐隐夹杂着我依了你便是你这冤孽,谁叫我离不得你,越说越不成调。
裴行俭转身便走,走了几步,却发现不对,回头才发现麴崇裕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就如突然化成了窑dòng边的一座雕塑。
--
差役们闻言才松了手,只留下两人站在孔大郎的左右。孔大郎抹了抹脸上的尘土,依然恨恨的看着义照,只是到底不敢再扑过去。姜氏和令氏此时一个比一个哭得厉害。裴行俭却默然看着下面的乱象,也不知在想什么。
麴崇裕走上一步,淡淡的笑道,这案子真真越发有趣了,不知裴长史该如何了断?
裴行俭摇了摇头,有悖人伦,莫过于此,何趣之有?扬声道,令氏,你有何可说?
令氏慢慢止住了哭泣,伏地回道,启禀裴长史,小妇人的儿媳姜氏不守妇德,生xingbào躁,时常rǔ骂于我,又污蔑高僧,今日小妇人是忍无可忍,才告发了这恶媳。小妇人的儿子好吃懒做,对小妇人无甚奉养,又纵容儿媳无礼,望长史为小妇人做主。声音略有些颤抖,却愈发显得悲凉。
孔大郎呆了一下,似乎万万没料到母亲不但没松口,反而添上了自己,高声叫了一句,阿娘!嗓音已全然变音。姜氏也瞪大眼睛看着令氏,不知是愤怒还是害怕,全身都在发抖。
都护府外诸人有xing急的便呸了一声,这孔大郎为护着自己妻子竟能向僧人动手,可见平日定然也不是个孝顺的!
裴行俭语气沉肃,令氏,你是要告儿媳忤逆,儿子奉养不周?你可知忤逆乃是死罪,奉养不周要徒三年?
麴崇裕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嗤笑,别的罪状也罢了,这忤逆不孝要入罪,便是村夫村妇也人人知晓的,他裴行俭还想拦着人告状不成?
令氏脸色发白,沉默半晌,颤声道,小妇人着实是活不下去日后便是自己下地做活挣命,也胜过这般苦熬!请长史做主!说着伏地痛哭。
裴行俭看向姜氏,姜氏,你还未问完,姜氏突然眼睛一翻,身子一软,昏了过去。
孔大郎并没有看姜氏,只张大嘴看着母亲,突然叫道,母亲,你真是要阿姜死么?你真要儿子流放三年?你
令氏猛的抬起头来,盯着他,你便这般不容我活下去?事到如今,还是要忤逆于我么!
孔大郎顿时说不出话来,脸色渐渐变得一片灰白。
裴行俭皱眉半响,叹了口气,来人,把孔大郎和姜氏收押,好生看管。
麴崇裕在一边看着他的脸色,嘴角眉梢都扬得高了几分,转头问对朱阙此案如此明白,裴长史为何不当堂判决?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身边数人听见。
裴行俭恍若无闻,声音平静的对下面的令氏道,令氏,本官会秉公办理此案,你们一家原是外迁之户,并无亲族,姜氏忤逆,论律当绞,而孔大郎要徒三年,姜氏无人收尸,你今日回去便准备一口棺木,明日棺木运到,本官便判决。你这便下去准备吧!
朱阙点了点头,低声对麴崇裕道,还是长史考虑周全。麴崇裕心qíng甚好,笑了笑也未做声。
令氏磕头谢恩,抹着眼泪往外而去,门外看热闹之人,都自觉的闪出一条道来,不少人还同qíng的叹息了几声,裴行俭的目光落在她的背影上,神色里一片漠然。
大佛寺的寺主法谦法师上前一步,合十行礼,长史,孔家家门出此不幸,令檀越孤苦无依,大佛寺不愿再追究欠租,愿撤销诉状。
裴行俭点头一笑,多谢大师体恤。只是此事既由贵寺诉状而起,明日还请义照大僧来做个见证,有劳了。
法谦微一犹豫,点了点头,与脸色好容易回转红润的义照一同告退而去。人群再次闪开极宽的一条路,不少人都神色恭敬的低头行礼。又见都护府里差役已经开始收拾院子,这才jiāo头接耳的慢慢散去。
麴崇裕收回目光,神色愈发愉悦,挑眉看了看从案几后站起身来的裴行俭,长史这案断得gān净利落,与以前大不相同。那件jī毛蒜皮的案子他生生拖了两日,这件忤逆大案他却是断得痛快!不过再快却也挡不住此事流传了。
裴行俭本来略有些出神,听了这话,倒是笑了起来,此案原本极是明白,又无证人可询,自与他案不能相提并论。又温言笑道,不知世子今夜可是有暇?
麴崇裕微微一愣,长史有事?
裴行俭点了点头,下官得了一壶好酒,只是喝的时辰地方都会有特别的讲究,世子若是有暇,正想邀世子同饮。
麴崇裕长长的喔了一声,看着裴行俭,凤目微眯,眼神深邃,守约还有此等雅兴?我一定奉陪!
时近五月,西州的白日已变得颇为漫长,好容易天色才彻底黑下来。残月还未升起,漫天的星斗却分外明亮。星光照在离西州不过十余里地的山壁上,让那些黑漆漆的窑dòng便如一只只黑色的眸子,似乎都在默默注视着山脚下那处并不明亮的灯火。
在一处离地面一丈多高的窑dòng里,黑暗寂静之中,却隐隐有一缕酒香飘dàng。裴行俭和麴崇裕都坐在窑dòng口上,一人手里拿着一个酒囊,借着外面的星光,不时喝上一口。
麴崇裕的玉狮子和裴行俭的坐骑早已被随行的府兵远远的带到了山后,带的酒囊也已经空了大半,麴崇裕终于不耐烦的叹了口气,裴长史,你这酒自然是好的,不过恕崇裕迟钝,你选的地方时辰,我却看不出妙处来。
他的身上穿了一件披风,只是这野外的夜风一chuī,那凉意似乎依然可以直入骨髓半夜三更来这种鬼地方喝酒,他真是疯了才会相信裴行俭的话!
裴行俭声音笃定,世子莫急,在此喝酒,与众不同之处转眼便知。
麴崇裕冷冷道,裴长史果然风雅,就夜风喝冷酒,也能悠然自得,崇裕佩服得紧。而且大路不走,偏要偏鬼鬼祟祟的走小道,进了这窑dòng,又是一坐半天,火褶都不让点,说是特意来喝酒,简直是见鬼,说是做贼倒是差不多。可这地方除了一片果园,几处菜园,一户人家以及无数荒废的窑dòng外,什么都没有,难不成他们是来偷瓜的?
在窑dòng外照进来的微弱星光中,裴行俭突然身子一动,指向一处地方,来了!
麴崇裕诧异的转头看了过去,只见那户人家的大门一看,屋里的灯光倾泻了出来,随即门又合上,有马灯的光线一晃一晃的向这边山壁而来。麴崇裕不由直起了身子,难不成裴行俭约了人半夜在窑dòng相见?
只见裴行俭果然站了起来,世子请跟我来。一口饮尽酒囊里的残酒,丢下酒囊,轻巧的跳了下去。
麴崇裕在进这窑dòng时便知,这位外貌儒雅的裴长史居然颇有身手,此时也不甘示弱,翻身跳落岩下。
裴行俭压低了声音,咱们过去,莫惊动了他们。
麴崇裕心头一动,念头急转,突然有几分明白过来,猛地收住了脚步,裴长史,你带我过来,可是发现今日的案子有古怪之处?
裴行俭回头看向他,果然瞒不了世子,不如世子稍候片刻,让下官过去看看便回?
麴崇裕一声冷笑,知道裴行俭这句话是以退为进,可心里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涌了上来,默然片刻还是淡淡的道,既然来了,一同过去便是。
窑dòng下的小路似乎已多年无人走动,只是对于这两人来说,却不是问题,两人沿着山壁一路往下,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响动。那晃动的马灯不久便接近了山崖最靠下面一处窑dòng,在窑dòng的灯光中无声无息的熄灭。
麴崇裕此时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成,想到白天的一幕,只觉得胸口一团怒火腾的烧了起来。
眼见离山壁上唯一有灯光的那处窑dòng只有十几步远,裴行俭回身打了个手势,两人脚步愈轻,悄然接近了窑dòng的窗口。
只听女子的抽泣之声从窗子里隐隐传了出来,又有男子的声音道,好了,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只是今日你也看见,你既然告了姜氏忤逆,你家大郎虽然孝顺你,却是要跟我拼命的。
那女声顿了一顿,才泣道,若不是看出这一点,你当我忍心叫他流放三年?那是我怀胎十月养下的儿子,如今看我便像仇人一般都是为了你这冤孽!
那男子叹了口气,心肝儿,我知晓你的难处,日后定会好好待你,我回头便跟上座禀告你孤苦可怜,没有这些田地租种,只怕活不下去,上座定然会允许你续租下去,说不定还会减些租子。咱们就在这里守着田地,一个外人没有,再不用似以前般偷偷摸摸,岂不是神仙般的日子?顿了顿又道,你也不早些跟我说,那姜氏,你告个不孝也就罢了,何必要说忤逆?
女声顿时锐利起来,怎么,你舍不得?你当我不知晓你打的什么主意?你哪日里不寻机跟那骚蹄子说几句,她一见你便脸红,都当我是瞎子么?这还没上手的,自然是分外惦记些,你若不甘心,去官府告了我便是,咱们两条命换她一条如何,你她越说声音越高,突然呜呜两声,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片刻之后,那男声才重新响了起来,你说什么昏话?一不做二不休,到了如今的田地,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今日连城里都不住要过来,便是要告诉你,明日无论怎样,你都不能心软。便是大郎嚷出咱们的事qíng,你也一口咬定他是为了救自家媳妇污蔑于你!
女声带点迟疑,若是那样大郎会不会
男声狠狠的道,诬告父母,自是恶逆的死罪,大郎今日还算识相,我只怕他明日见姜氏要被绞杀,昏了头,什么话都会往外倒,你却绝不能心软,不但不能松口,连神色都不能露一点风出来,那裴长史听说是个极厉害的,今日他是后头才赶到,不然你我只怕还不会如此顺遂。
女声停了半晌,带上了哭音,可是大郎
男人道,我也不愿如此,只是事到如今,你若舍不得他死,那便是咱们永世不能在一起,你可舍得?如今只要打发了那两个,咱们便是活神仙一般说着说着,里面的动静变得古怪起来,那女子的哭音也渐渐变成了喘息,隐隐夹杂着我依了你便是你这冤孽,谁叫我离不得你,越说越不成调。
裴行俭转身便走,走了几步,却发现不对,回头才发现麴崇裕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就如突然化成了窑dòng边的一座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