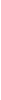从西州北边的大佛寺到南面的曲水坊,原本只有一里来地,琉璃和小檀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却足足走了一刻钟才到。待进了院门,琉璃的额头都有些微微见汗了,小檀更是一迭声要院中的仆妇赶紧打上些井水来,好解渴去热。
阿燕听得声音,从灶房里探出头,娘子回来啦。又对小檀笑道这才几月,你便热成了这般模样,真要入了夏,看你怎么过!
琉璃笑道,再打口井,让她住里边便是!
小檀愁眉苦脸的叹了口气,正是,听说真到了夏日,咱们这里在屋顶上放个jī蛋,一炷香的工夫便能熟透了,偏偏这西州城里连冰盆都无处买去,只怕真要住在井里才过得。
琉璃摇了摇头,谁说咱们这里没有冰,你想用冰也不难!
小檀忙惊喜的看向琉璃,琉璃一本正经的道,只要你剃去一头青丝,进大佛寺做个比丘尼,不就有冰用了?今日你不还要请经回来么,可见是有佛缘的!
小檀张口结舌,想起今日刚刚听说大佛寺乃是西州城唯一有冰窖之所,不由嗔道,娘子又打趣我!停了停又嘀咕了一句,那是大佛寺,又不是尼庵!
一院子人顿时都笑了起来。
琉璃便问阿琴,午膳的冷淘可是已备好了,见阿琴点了点头,便准备往上房去。阿琴却突然哎呀了一声,阿郎出去用素斋了,说是世子有请!
麴孔雀?琉璃不由皱起了眉头,这人怎么处处yīn魂不散?自己是不是要想个法子把他也气个中风,才能过上几天安静的日子?
与大佛寺一墙之隔的普照寺里,前院的斋饭早已开桌,每一桌都挤得满满当当,后院的禅房却是一片安静,每间屋里坐着三五不等的香客,各个打扮不凡。最里面的一间禅房里,案几上已摆上了四五样jīng致的斋菜,小小的银壶里,则是自酿的酒水。案几边只坐了两个男子,穿着米色长袍束着紫金带的那位正动作优雅的持壶给自己面前的酒盏里满上美酒,手上却突然顿了一顿。
坐在他对面蒲团上的男子恍若不觉的端起了面前的酒杯,看着里面的酒水,点了点头,色如琥珀,香似兰麝,世子说得不错,这普照寺酿的酒水,果然是难得的佳品。
麴崇裕淡淡的笑了笑,他适才背上突然起了一层寒栗,只是那感觉来得快,去得也快,此时也不及多想,依然稳稳的将酒水倒了满杯,头也不抬的道,长史不是西州人,自然不知这普照寺虽小,斋菜和酒水却是西州第一,因此我每年此日都是先去大佛寺献上供奉,随后便来此用斋。
裴行俭微笑着点点头,世子的眼光果然jīng准。
麴崇裕的眉梢不由微微一挑,眼里浮现出一丝自嘲之色,长史这是在取笑我么?
裴行俭抬头看着麴崇裕,哪里,适才才下经过路口,见了世子的舍经之棚,心里实在佩服得很。
麴崇裕眼中嘲讽之色更浓,雕虫小技,何足挂齿!若论深谋远虑,我拍马也及不上裴长史。长史今日一路过来,岂不知西州人如今看待长史,与看待佛经也无甚差别?长史的胸怀谋略,崇裕每一念及,便佩服得五体投地。
裴行俭摇了摇头,世子何必过谦?裴某初来乍到,不过是做了几件有些骇世惊俗之事,一时被大伙儿议论得多些,也是在所难免,但认真论根基论人望,却差世子远矣。记得当日途经大沙海,便是村中小童,也知世子之仁善。这几个月来,裴某屡见世子凡事均以西州为先,心里着实十分佩服。大唐官员虽多,能宅心仁厚、爱民如子如世子者,也是少有。
麴崇裕看了裴行俭一眼,见他的神色极为认真,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得随口说了声长史过奖,又举起了手中的杯盏,长史请。
裴行俭喝了一口,微微点头,果然醇厚绵长。见麴崇裕并不说话,他也随意喝酒用菜,偶然品评几句,谈笑从容,却是绝口不问麴崇裕请他吃斋所为何来,当真便如只是与好友来寺中小聚一般。
眼见酒壶已换到第二个,麴崇裕忍不住微微挪了挪膝盖,给裴行俭满酒时漫不经心般道,适才崇裕在大佛寺时,遇到了上座觉玄法师,法师还问起过,大佛寺僧人相讼之案,都护府何时开审,如何开审,却不知长史如今怎么打算?
裴行俭也是一脸的不以为意,此案在下不曾过问太多,听朱参军的意思是,此事不过是财物相争口角之辩的小案,只是既然事涉大佛寺,还是要谨慎一些,最好就如盗牛案一般公开审理,也好服众。
麴崇裕心里冷笑了一声,面上露出了几分忧色,如此,只怕不大妥当吧?
裴行俭略有些意外,依世子之见,此案当如何审理?
麴崇裕正色道,长史应当也知,西州信徒众多,大佛寺又是地位超然,如今寺中僧人传出争夺财物、互相诽谤之事,颇损于佛院清誉。
裴行俭眉头微皱,世子的意思是,把此事压下?
麴崇裕摇头道,既然都护府已收到诉状,岂有不审之理?但都护和觉玄法师的意思都是,为免口舌议论,审理此案时,除却相关之人,闲杂人等还是屏退才好。说完目光便落在裴行俭的脸上,静静的等着他的反驳。
裴行俭的脸上果然流露出了几分为难之色,那都护的意思难道是,以后但凡涉及僧尼之案,都要照此而行?
麴崇裕心里微松,都护绝无此意,这一桩案子原是有些不同,两位方外之人在公堂上为些言语财物之事相争不下,实在不宜让信徒们瞧见。至于旁的案子却是不必如此,同是大佛寺之案,像欠租的那一桩,长史照常审理便是,不用顾忌于大佛寺。裴行俭是想给他下套么?他才不会钻!
裴行俭沉吟片刻,点了点头,世子所言,的确不无道理,在下回去便吩咐朱参军照此办理。
麴崇裕不由吃了一惊,顿了顿才道,如此甚好,多谢长史。看着裴行俭的眼神多少流露出了些许狐疑。
从火烧欠单到如今,已过去了将近一个月,眼前的这位裴长史居然日日都不慌不忙的在府衙里处理公务,每日发布的政令不是兴修水利,就是督促州学,仿佛根本就没想过要去想法子筹备军粮,身边的庶仆们则是四处乱窜,混迹于市井之中,三天两头的不见踪影。他自然是有些摸不着头脑,直到几天前得知大佛寺僧人相讼之事已被传得纷纷扬扬,而另一桩极简单的大佛寺告租户欠租的小案却被一拖再拖,才隐隐觉得不对若论财力雄厚,大佛寺自然是西州第一,裴行俭难道是把主意打到了这上面,因此才故意要令佛院为难?可若是真是如此,他又怎会这般痛快就答应了下来?
裴行俭悠然的喝了口酒,抬眼笑道,世子可是疑心在下耍jian?世子放心,裴某虽然不信释教,却也不至于成心去为难佛院,定然会秉公执法,绝不会令佛寺与信徒们寒心。
麴崇裕顿时有些无趣,只得笑了笑,长史哪里话,长史一心为公,原是人人皆知的。
裴行俭瞅了他片刻,突然呵呵一笑,世子如此相问,还是有些不放心军粮之事吧?昨日我已禀告过都护,西州府兵人手有限,差役也不多,今秋的军粮裴某打算jiāo由西州行商收购运送,府兵略行押送之事即可,都护也已应了,此事想来已不必太过担忧。
麴崇裕心中微震,裴行俭竟是要挑明了说么?随意点头道,长史的主意甚妙。此事他自然早已知晓,若让他来主持此事,也会如此处置。以西州行商们那番上天入地的本事,只要有利可图,做起事来原比官府更是可靠,只是,如此一来,钱又该从哪里出?他忍不住眯了眯眼睛,只是崇裕有一事不解,还望长史指教。
裴行俭似乎早有准备,笑得异常坦然,世子但言无妨。
麴崇裕的眼睛紧紧的盯在了对面这张神qíng从容的脸上,不知支付军粮的钱帛,长史打算如何筹备?
裴行俭微微一怔,随即便笑了起来,世子原来是在担心这个。他举杯饮了一口,眉眼间一片舒展,此事裴某早已算过,今秋之前,必有西州贵人慷慨解囊,我等不用忧心,只要把钱仓备好便是。
这叫什么话?麴崇裕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裴行俭是把自己当三岁的小孩么?他的那些把戏,别人看不透,自己还看不透?从白三的血光之灾到韩四的自投罗网,那些故弄玄机的背后,都是深不可测的心机和算计!他还以为自己也和那些愚民一般,相信了那些鬼话?这军粮需要的筹备的钱帛,少说也要两三万缗,西州顶尖的高门豪富十几年前都被唐人押到了长安,如今休养生息也不过数载,有几家能出得起这笔钱,谁又会疯到自动拿出这笔钱?
麴崇裕忍不住冷笑起来,长史果然是胸有丘壑!只是西州非比长安,似长史般挥手便能捐出十几万缗之人,麴某尚未听闻,长史不肯见教也便罢了,还是莫拿虚言来搪塞!
裴行俭诧异的看了麴崇裕一眼,笑道,世子此言差矣,裴某虽是不才,却何时曾拿虚言搪塞于人?
麴崇裕冷笑不语。裴行俭叹了口气,世子,你若实在不信,咱们不如赌上一赌?
跟他打赌?麴崇裕警惕的抬起头来,裴行俭却自顾自的一路说了下去,今秋之前,若无西州贵人捐出这笔钱帛来,裴某此后便再不过问西州政事,自行上书请罪,世子你看如何?
麴崇裕不由哈哈大笑,长史不必多说,今秋之前,想来自有人相助长史,麴某岂敢不信?他裴行俭能把十几万缗拿来做局,库狄氏又是那么个厉害角色,想来身家不会太薄,安氏家族又是根基深厚,到时每家凑一些,拿出两三缗来只怕不是很难,又何必虚言相托于西州贵人。
裴行俭摇头笑道,世子莫不是以为裴某会自行筹钱,或是令亲眷相助,说来这也的确不失为一策,只是据裴某推算,这相助之人身份高贵,在西州一言九鼎、威望极高,裴某是万万不及的,若不是此等人物相助,自然算是裴某输了这一局!
麴崇裕眉头微皱,身份高贵、一言九鼎,难道他说的是自己的父亲?可父亲怎么会给他这笔钱?低头略想了片刻,他忍不住道,若是真有此等人物相助于长史,长史又要崇裕做什么?
--
阿燕听得声音,从灶房里探出头,娘子回来啦。又对小檀笑道这才几月,你便热成了这般模样,真要入了夏,看你怎么过!
琉璃笑道,再打口井,让她住里边便是!
小檀愁眉苦脸的叹了口气,正是,听说真到了夏日,咱们这里在屋顶上放个jī蛋,一炷香的工夫便能熟透了,偏偏这西州城里连冰盆都无处买去,只怕真要住在井里才过得。
琉璃摇了摇头,谁说咱们这里没有冰,你想用冰也不难!
小檀忙惊喜的看向琉璃,琉璃一本正经的道,只要你剃去一头青丝,进大佛寺做个比丘尼,不就有冰用了?今日你不还要请经回来么,可见是有佛缘的!
小檀张口结舌,想起今日刚刚听说大佛寺乃是西州城唯一有冰窖之所,不由嗔道,娘子又打趣我!停了停又嘀咕了一句,那是大佛寺,又不是尼庵!
一院子人顿时都笑了起来。
琉璃便问阿琴,午膳的冷淘可是已备好了,见阿琴点了点头,便准备往上房去。阿琴却突然哎呀了一声,阿郎出去用素斋了,说是世子有请!
麴孔雀?琉璃不由皱起了眉头,这人怎么处处yīn魂不散?自己是不是要想个法子把他也气个中风,才能过上几天安静的日子?
与大佛寺一墙之隔的普照寺里,前院的斋饭早已开桌,每一桌都挤得满满当当,后院的禅房却是一片安静,每间屋里坐着三五不等的香客,各个打扮不凡。最里面的一间禅房里,案几上已摆上了四五样jīng致的斋菜,小小的银壶里,则是自酿的酒水。案几边只坐了两个男子,穿着米色长袍束着紫金带的那位正动作优雅的持壶给自己面前的酒盏里满上美酒,手上却突然顿了一顿。
坐在他对面蒲团上的男子恍若不觉的端起了面前的酒杯,看着里面的酒水,点了点头,色如琥珀,香似兰麝,世子说得不错,这普照寺酿的酒水,果然是难得的佳品。
麴崇裕淡淡的笑了笑,他适才背上突然起了一层寒栗,只是那感觉来得快,去得也快,此时也不及多想,依然稳稳的将酒水倒了满杯,头也不抬的道,长史不是西州人,自然不知这普照寺虽小,斋菜和酒水却是西州第一,因此我每年此日都是先去大佛寺献上供奉,随后便来此用斋。
裴行俭微笑着点点头,世子的眼光果然jīng准。
麴崇裕的眉梢不由微微一挑,眼里浮现出一丝自嘲之色,长史这是在取笑我么?
裴行俭抬头看着麴崇裕,哪里,适才才下经过路口,见了世子的舍经之棚,心里实在佩服得很。
麴崇裕眼中嘲讽之色更浓,雕虫小技,何足挂齿!若论深谋远虑,我拍马也及不上裴长史。长史今日一路过来,岂不知西州人如今看待长史,与看待佛经也无甚差别?长史的胸怀谋略,崇裕每一念及,便佩服得五体投地。
裴行俭摇了摇头,世子何必过谦?裴某初来乍到,不过是做了几件有些骇世惊俗之事,一时被大伙儿议论得多些,也是在所难免,但认真论根基论人望,却差世子远矣。记得当日途经大沙海,便是村中小童,也知世子之仁善。这几个月来,裴某屡见世子凡事均以西州为先,心里着实十分佩服。大唐官员虽多,能宅心仁厚、爱民如子如世子者,也是少有。
麴崇裕看了裴行俭一眼,见他的神色极为认真,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得随口说了声长史过奖,又举起了手中的杯盏,长史请。
裴行俭喝了一口,微微点头,果然醇厚绵长。见麴崇裕并不说话,他也随意喝酒用菜,偶然品评几句,谈笑从容,却是绝口不问麴崇裕请他吃斋所为何来,当真便如只是与好友来寺中小聚一般。
眼见酒壶已换到第二个,麴崇裕忍不住微微挪了挪膝盖,给裴行俭满酒时漫不经心般道,适才崇裕在大佛寺时,遇到了上座觉玄法师,法师还问起过,大佛寺僧人相讼之案,都护府何时开审,如何开审,却不知长史如今怎么打算?
裴行俭也是一脸的不以为意,此案在下不曾过问太多,听朱参军的意思是,此事不过是财物相争口角之辩的小案,只是既然事涉大佛寺,还是要谨慎一些,最好就如盗牛案一般公开审理,也好服众。
麴崇裕心里冷笑了一声,面上露出了几分忧色,如此,只怕不大妥当吧?
裴行俭略有些意外,依世子之见,此案当如何审理?
麴崇裕正色道,长史应当也知,西州信徒众多,大佛寺又是地位超然,如今寺中僧人传出争夺财物、互相诽谤之事,颇损于佛院清誉。
裴行俭眉头微皱,世子的意思是,把此事压下?
麴崇裕摇头道,既然都护府已收到诉状,岂有不审之理?但都护和觉玄法师的意思都是,为免口舌议论,审理此案时,除却相关之人,闲杂人等还是屏退才好。说完目光便落在裴行俭的脸上,静静的等着他的反驳。
裴行俭的脸上果然流露出了几分为难之色,那都护的意思难道是,以后但凡涉及僧尼之案,都要照此而行?
麴崇裕心里微松,都护绝无此意,这一桩案子原是有些不同,两位方外之人在公堂上为些言语财物之事相争不下,实在不宜让信徒们瞧见。至于旁的案子却是不必如此,同是大佛寺之案,像欠租的那一桩,长史照常审理便是,不用顾忌于大佛寺。裴行俭是想给他下套么?他才不会钻!
裴行俭沉吟片刻,点了点头,世子所言,的确不无道理,在下回去便吩咐朱参军照此办理。
麴崇裕不由吃了一惊,顿了顿才道,如此甚好,多谢长史。看着裴行俭的眼神多少流露出了些许狐疑。
从火烧欠单到如今,已过去了将近一个月,眼前的这位裴长史居然日日都不慌不忙的在府衙里处理公务,每日发布的政令不是兴修水利,就是督促州学,仿佛根本就没想过要去想法子筹备军粮,身边的庶仆们则是四处乱窜,混迹于市井之中,三天两头的不见踪影。他自然是有些摸不着头脑,直到几天前得知大佛寺僧人相讼之事已被传得纷纷扬扬,而另一桩极简单的大佛寺告租户欠租的小案却被一拖再拖,才隐隐觉得不对若论财力雄厚,大佛寺自然是西州第一,裴行俭难道是把主意打到了这上面,因此才故意要令佛院为难?可若是真是如此,他又怎会这般痛快就答应了下来?
裴行俭悠然的喝了口酒,抬眼笑道,世子可是疑心在下耍jian?世子放心,裴某虽然不信释教,却也不至于成心去为难佛院,定然会秉公执法,绝不会令佛寺与信徒们寒心。
麴崇裕顿时有些无趣,只得笑了笑,长史哪里话,长史一心为公,原是人人皆知的。
裴行俭瞅了他片刻,突然呵呵一笑,世子如此相问,还是有些不放心军粮之事吧?昨日我已禀告过都护,西州府兵人手有限,差役也不多,今秋的军粮裴某打算jiāo由西州行商收购运送,府兵略行押送之事即可,都护也已应了,此事想来已不必太过担忧。
麴崇裕心中微震,裴行俭竟是要挑明了说么?随意点头道,长史的主意甚妙。此事他自然早已知晓,若让他来主持此事,也会如此处置。以西州行商们那番上天入地的本事,只要有利可图,做起事来原比官府更是可靠,只是,如此一来,钱又该从哪里出?他忍不住眯了眯眼睛,只是崇裕有一事不解,还望长史指教。
裴行俭似乎早有准备,笑得异常坦然,世子但言无妨。
麴崇裕的眼睛紧紧的盯在了对面这张神qíng从容的脸上,不知支付军粮的钱帛,长史打算如何筹备?
裴行俭微微一怔,随即便笑了起来,世子原来是在担心这个。他举杯饮了一口,眉眼间一片舒展,此事裴某早已算过,今秋之前,必有西州贵人慷慨解囊,我等不用忧心,只要把钱仓备好便是。
这叫什么话?麴崇裕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裴行俭是把自己当三岁的小孩么?他的那些把戏,别人看不透,自己还看不透?从白三的血光之灾到韩四的自投罗网,那些故弄玄机的背后,都是深不可测的心机和算计!他还以为自己也和那些愚民一般,相信了那些鬼话?这军粮需要的筹备的钱帛,少说也要两三万缗,西州顶尖的高门豪富十几年前都被唐人押到了长安,如今休养生息也不过数载,有几家能出得起这笔钱,谁又会疯到自动拿出这笔钱?
麴崇裕忍不住冷笑起来,长史果然是胸有丘壑!只是西州非比长安,似长史般挥手便能捐出十几万缗之人,麴某尚未听闻,长史不肯见教也便罢了,还是莫拿虚言来搪塞!
裴行俭诧异的看了麴崇裕一眼,笑道,世子此言差矣,裴某虽是不才,却何时曾拿虚言搪塞于人?
麴崇裕冷笑不语。裴行俭叹了口气,世子,你若实在不信,咱们不如赌上一赌?
跟他打赌?麴崇裕警惕的抬起头来,裴行俭却自顾自的一路说了下去,今秋之前,若无西州贵人捐出这笔钱帛来,裴某此后便再不过问西州政事,自行上书请罪,世子你看如何?
麴崇裕不由哈哈大笑,长史不必多说,今秋之前,想来自有人相助长史,麴某岂敢不信?他裴行俭能把十几万缗拿来做局,库狄氏又是那么个厉害角色,想来身家不会太薄,安氏家族又是根基深厚,到时每家凑一些,拿出两三缗来只怕不是很难,又何必虚言相托于西州贵人。
裴行俭摇头笑道,世子莫不是以为裴某会自行筹钱,或是令亲眷相助,说来这也的确不失为一策,只是据裴某推算,这相助之人身份高贵,在西州一言九鼎、威望极高,裴某是万万不及的,若不是此等人物相助,自然算是裴某输了这一局!
麴崇裕眉头微皱,身份高贵、一言九鼎,难道他说的是自己的父亲?可父亲怎么会给他这笔钱?低头略想了片刻,他忍不住道,若是真有此等人物相助于长史,长史又要崇裕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