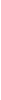第157页
他说上头不允许百姓私下祭祀,因为京城里已经请了天师做法,瘟神很快就走了。
薛遥知道瘟神不可能很快送走,便对老百姓们说:你们这种祭祀方法非但不会送走瘟神,参与的人还会招来瘟神。
当然没人相信他这贵族打扮的少年人的狂言。
但老百姓不敢跟官府闹,见县太爷软硬兼施,也就乖乖撤了祭台。
然而,大概是因为搭建祭台的人当中,有潜伏期的患者,当天回去后,又有七户人家出现了瘟疫症状的患者。
有人猜测是原本送瘟神的祭祀取消,还拆了祭台,导致瘟神降罪,要带走更多人命。
于是,老百姓们火急火燎地又开始重新准备祭祀。
薛遥赶忙再去衙门,要求知县再次出面阻挠。
这一次,老百姓们不那么好糊弄了,官府动用武力驱散民众,还抓了几个带头闹事者进牢房,才又平息下去。
太医们每天出诊,都有薛遥安排的太监,监视他们戴口罩和洗手。
这为他们性命着想的举措,却让很多太医忍气吞声,觉得薛遥这古怪少年仗着太子的面子,有意戏弄折辱他们。
薛遥来到平榕县,从来不出诊也不探讨配方,除了强制大夫们蒙面和洗手之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打压当地想要集会祭祀的老百姓。
可以想象,太医私下里对这个年轻人的印象,已经差到了极致。
薛遥对此无法解释,只能淡定地该吃吃该睡睡,躺在家中等兵符。
就在这天夜里,薛遥熟睡之中,隐约觉得一股寒气凉飕飕的往脖子里钻。
迷迷糊糊地把被子往上拉了拉,手背忽然撞到一个凉飕飕的东西。
薛遥浑身一紧,缓缓睁开眼。
三更半夜没开窗,月色也透不进来,一片漆黑之中,却能看见一双反射着几点光泽的双眼,正杀气腾腾地注视着自己。
薛遥一瞬间血往头顶窜,头皮都发麻了。
别出声。一个带着乡音的陌生男人嗓音。
薛遥屏住呼吸,眼睛渐渐适应黑暗床边站着一个衣着朴素的壮汉,葛巾蒙着脸,只露出一双眼睛,拿着种地用的镰刀架在他脖子上。
冷静一点。薛遥尽量让自己嗓音舒缓。
冷静个球!这壮汉浑身都在发抖,不知道是畏惧还是激动,我爹刚走三个时辰,我让你这杀千刀的狗官给他陪葬!都是你这狗官不许咱们送瘟神!
你不要激动。薛遥一动不动躺在床上与他对视:我并不是当官的,也不是不让你们送瘟神,而是不希望你们招来瘟神。
放屁!那壮汉一脸惊怒,气喘吁吁地低斥:不是当官的,那县太爷为啥听你的!就是你让拆了祭台,我爹才惹毛了瘟神老爷!你这狗官!你这狗官!
他说着,愈发情绪激动,握紧了镰刀,目露凶光。
薛遥看出他准备使力割开自己喉咙,立即开口道:想想你的妻儿!
刚准备行凶的壮汉一愣,顿住镰刀问他:我妻儿咋了?你要那他们怎地!
杀了我你全家都得死。
谁晓得是我杀的?我杀了你这狗官,再爬墙出去!
薛遥唬他道:仵作一看刀口,就知道是你家的镰刀杀了人。
壮汉闻言一哆嗦,低头看向自己的镰刀,又抬头怒道:我扔河里去!
薛遥试探道:买新镰刀?
对!买把新的,谁瞧得出来?
捕头一看,就你家换了新镰刀,哪能不知道是你杀的人?
断案哪里这么容易?但薛遥觉得这男人看起来头脑简单,应该很好骗。
壮汉果真被他唬住了,抓着镰刀的手不住哆嗦。
屋里除了壮汉的喘息声,就剩薛遥擂鼓般的心跳声。
脑子里此刻乱极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在转。
万万没想到,会这么不明不白死在陌生人手里。
他想救人,却被救助者误解。
如果这把镰刀砍下来,他重活这一世的意义是什么?
太子的地位没保住。
龙傲天幼崽还被他养成了哈士奇。
怎么办?
好不甘心。
你冷静一些,我不是官,我大老远从京城赶来平榕县,就是为了来救你们。
薛遥坦诚地注视着壮汉:上回来,给你们发放的低息粮食,就是我不远千里从江浙拼命筹集的。你借粮了吗?记不记得?登记的时候我就坐在衙役后头的茶几旁,以免衙役动手脚贪老百姓便宜。
那壮汉渐渐睁大眼,仔细辨认薛遥的脸。
可事实上,薛遥监督放粮,并不是一直在场,大部分农民根本没见过他。
薛遥心里觉得有戏,一个冒着生命危险替父报仇的农民,能坏到哪里去呢?再忽悠忽悠,说不定命就保住了。
我外祖父是京城的高官,心系百姓,我祖籍江苏,八辈子跟平榕县扯不上关系,无怨无仇的,我干嘛要害这里的老百姓?薛遥继续讲道理:反倒是上百万石的粮食,我借给受灾三县,说句难听的话,老百姓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不是血本无归了?
--
薛遥知道瘟神不可能很快送走,便对老百姓们说:你们这种祭祀方法非但不会送走瘟神,参与的人还会招来瘟神。
当然没人相信他这贵族打扮的少年人的狂言。
但老百姓不敢跟官府闹,见县太爷软硬兼施,也就乖乖撤了祭台。
然而,大概是因为搭建祭台的人当中,有潜伏期的患者,当天回去后,又有七户人家出现了瘟疫症状的患者。
有人猜测是原本送瘟神的祭祀取消,还拆了祭台,导致瘟神降罪,要带走更多人命。
于是,老百姓们火急火燎地又开始重新准备祭祀。
薛遥赶忙再去衙门,要求知县再次出面阻挠。
这一次,老百姓们不那么好糊弄了,官府动用武力驱散民众,还抓了几个带头闹事者进牢房,才又平息下去。
太医们每天出诊,都有薛遥安排的太监,监视他们戴口罩和洗手。
这为他们性命着想的举措,却让很多太医忍气吞声,觉得薛遥这古怪少年仗着太子的面子,有意戏弄折辱他们。
薛遥来到平榕县,从来不出诊也不探讨配方,除了强制大夫们蒙面和洗手之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打压当地想要集会祭祀的老百姓。
可以想象,太医私下里对这个年轻人的印象,已经差到了极致。
薛遥对此无法解释,只能淡定地该吃吃该睡睡,躺在家中等兵符。
就在这天夜里,薛遥熟睡之中,隐约觉得一股寒气凉飕飕的往脖子里钻。
迷迷糊糊地把被子往上拉了拉,手背忽然撞到一个凉飕飕的东西。
薛遥浑身一紧,缓缓睁开眼。
三更半夜没开窗,月色也透不进来,一片漆黑之中,却能看见一双反射着几点光泽的双眼,正杀气腾腾地注视着自己。
薛遥一瞬间血往头顶窜,头皮都发麻了。
别出声。一个带着乡音的陌生男人嗓音。
薛遥屏住呼吸,眼睛渐渐适应黑暗床边站着一个衣着朴素的壮汉,葛巾蒙着脸,只露出一双眼睛,拿着种地用的镰刀架在他脖子上。
冷静一点。薛遥尽量让自己嗓音舒缓。
冷静个球!这壮汉浑身都在发抖,不知道是畏惧还是激动,我爹刚走三个时辰,我让你这杀千刀的狗官给他陪葬!都是你这狗官不许咱们送瘟神!
你不要激动。薛遥一动不动躺在床上与他对视:我并不是当官的,也不是不让你们送瘟神,而是不希望你们招来瘟神。
放屁!那壮汉一脸惊怒,气喘吁吁地低斥:不是当官的,那县太爷为啥听你的!就是你让拆了祭台,我爹才惹毛了瘟神老爷!你这狗官!你这狗官!
他说着,愈发情绪激动,握紧了镰刀,目露凶光。
薛遥看出他准备使力割开自己喉咙,立即开口道:想想你的妻儿!
刚准备行凶的壮汉一愣,顿住镰刀问他:我妻儿咋了?你要那他们怎地!
杀了我你全家都得死。
谁晓得是我杀的?我杀了你这狗官,再爬墙出去!
薛遥唬他道:仵作一看刀口,就知道是你家的镰刀杀了人。
壮汉闻言一哆嗦,低头看向自己的镰刀,又抬头怒道:我扔河里去!
薛遥试探道:买新镰刀?
对!买把新的,谁瞧得出来?
捕头一看,就你家换了新镰刀,哪能不知道是你杀的人?
断案哪里这么容易?但薛遥觉得这男人看起来头脑简单,应该很好骗。
壮汉果真被他唬住了,抓着镰刀的手不住哆嗦。
屋里除了壮汉的喘息声,就剩薛遥擂鼓般的心跳声。
脑子里此刻乱极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在转。
万万没想到,会这么不明不白死在陌生人手里。
他想救人,却被救助者误解。
如果这把镰刀砍下来,他重活这一世的意义是什么?
太子的地位没保住。
龙傲天幼崽还被他养成了哈士奇。
怎么办?
好不甘心。
你冷静一些,我不是官,我大老远从京城赶来平榕县,就是为了来救你们。
薛遥坦诚地注视着壮汉:上回来,给你们发放的低息粮食,就是我不远千里从江浙拼命筹集的。你借粮了吗?记不记得?登记的时候我就坐在衙役后头的茶几旁,以免衙役动手脚贪老百姓便宜。
那壮汉渐渐睁大眼,仔细辨认薛遥的脸。
可事实上,薛遥监督放粮,并不是一直在场,大部分农民根本没见过他。
薛遥心里觉得有戏,一个冒着生命危险替父报仇的农民,能坏到哪里去呢?再忽悠忽悠,说不定命就保住了。
我外祖父是京城的高官,心系百姓,我祖籍江苏,八辈子跟平榕县扯不上关系,无怨无仇的,我干嘛要害这里的老百姓?薛遥继续讲道理:反倒是上百万石的粮食,我借给受灾三县,说句难听的话,老百姓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不是血本无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