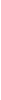云安只见过申王妃,便单在王妃身上想,二郎的话却是对她有所启发,说道:“那王妃也没说起过,要不我写信去问问父亲?你可知申王的名讳?我都写清楚,让父亲好好想想。”
小门小户的名姓难打听,这样地位煊赫的人家就根本不用打听,但毕竟是亲王之尊,二郎没有直呼,提来笔墨,写在了纸上,略去皇姓,只一个“珩”字。
云安看了点头,已在脑中思索如何写这封家书。可是,再一眼瞥见二郎,他却盯着自己的字愣住了,脸色也不对。
“二郎,不是这个字吗?”云安推了推这人。
二郎一时不动,良晌恍然回神,却将这写了“珩”字的纸收到了袖中:“云儿,我忽然想起来学中有事,要出去一趟。”
云安觉得有些突然,但郑梦观昨日便没去太学,今天要去也不算奇怪:“好,那你就快去吧。”
二郎举动果断,又带着几分急切,很快便离了人境院。素戴送走阿春后就在廊下闲坐,忽见此状,便进来问。云安与她随口说了,并不当回事,继续歪靠着看书。
素戴一笑,不过从旁侍奉,替她收拾一地的散简,取走吃空的盘碟,不觉说道:“周燕阁自从送了那一回紫萝糕,如今便隔三差五地送,我倒不信她的心诚,莫不是敢在这吃食里动手脚吧?”
云安轻嗤,道:“她哪里有这本事,都是云夫人替她做人呢!我以为你早就看出来了。但她若要害人,还放在自己送来的东西里,也太蠢了吧?况且我这不没事么,里头连个泻药也没有。”
“好吧,算我白忖度一回。”
素戴抿了抿唇,不再多想,便要将收好的空盘送去厨下,一转身,目光无意间划过了书房的南墙。那处摆着二郎的明光铠和长剑,还有那只绣了诗句的步靫。
素戴久久停驻,默不作声反引起了云安的注意,她也顺着看去,看到了那副明光铠。“你怎么了?每回进来都要看一眼。”
原来,素戴虽不常来书房侍奉,但只要云安在,二郎都会让她替代临啸。如此多次,云安便就发现过,素戴喜欢盯着那副铠甲,似乎显得比她还上心。
素戴顿觉窘迫,脸上一红,道:“我就是觉得,总觉得步靫上的字奇怪,那字的走针绣法,好像在哪里见过的。”
云安不通针线,皱眉说道:“又不是绣花,还有什么针法吗?”
“每个人下针都有自己的习惯,就像写字的字迹,每个人都不同。”素戴说着再三望了一眼南墙,只是仍无头绪,“罢了,针法相似的也多,夫人看书吧,我去了。”
云安才没有往心里去,应了声,重新沉浸到杂书的欢乐中。
第35章 欲留芳
郑梦观离开家,却非是要到太学,带着临啸一道,主仆二人的马蹄直向悲田院驰去。临啸不解主人用意,二郎也没有明言,及至抵达悲田院门首,二郎才谨慎地问起:
“我上回遣你来此打听一个叫王行的人,你除了知道他并非悲田院主事,可有觉出别的异常?”
临啸是有一说一的老实人,又岂敢对二郎隐瞒,只连忙摇头,道:“小奴都对公子如实说了,真正的主事叫蒋融,他说自己当了快十年的主事,从未听说过叫王行的人,也没见过陌生面孔。”
这话确是二郎第二次听了,却比上回听时更让他不踏实。他从袖中取出了那张写着“珩”字的纸,展开又盯了许久——把这个字拆开,不就是“王行”两个字吗?
若非云安无意间提问申王的名讳,二郎根本想不到这样的关联。设若王行就是申王,那他以亲王之尊躲在偏狭的悲田院里与人议事,却是意欲何为?
而对二郎来说更重要的是,王行亲近云安之意昭然若揭,便自探春宴起,申王府两次来邀,这没来由的“厚爱”,是否就是王行利用申王妃的名义,所使的障眼法呢?
想到此处,二郎将“珩”字纸张猛撕成两半,握在手心,攥得骨节发白。“你带路,我要见一见蒋主事。”
二郎努力克制住胸中的躁动,还要最后探一探虚实。临啸亦不难发觉主人的情绪有变,不敢动问,即刻便引路前去。
顷刻到了悲田院官吏的值房,说明来意,便有个差役请了主事出来。二郎没见过蒋捷,就看是个绿袍的中年人,可待要开口,临啸却将他拦住了,急道:
“公子,换人了!他不是蒋主事!”
二郎登时大惊,将心里的种种猜测一下压实了□□分。
看这主仆二人举动奇怪,那官人抚须一叹,有些不耐烦:“你们是何人啊?怎么不问清楚就来找人呢?蒋主事上个月就调了外任,如今这悲田院是我孙某人做主了!”
官员调动看似平常,又是这等品阶低微的官职,更似乎是不起眼的小事。然则偏偏是这个关口,那个做了十年主事的蒋捷就一下调走了,还是外任,一时是寻不着人的。
“那孙主事可知,蒋主事调往了何处?”二郎拱手一礼,问道。
“不知不知,我与蒋主事素不相识,不过接任而已。哪里来的后生?快走吧!”这孙主事本就懒得接待,又看并不是来找他的,大手一挥转回了值房。
果然询问无果,二郎只有另作计较,但他已经认定了,这个王行不会是旁人。离了悲田院,二郎没有返家,只叫临啸先回,自己又往从前的几位同窗家拜访去了。
--
小门小户的名姓难打听,这样地位煊赫的人家就根本不用打听,但毕竟是亲王之尊,二郎没有直呼,提来笔墨,写在了纸上,略去皇姓,只一个“珩”字。
云安看了点头,已在脑中思索如何写这封家书。可是,再一眼瞥见二郎,他却盯着自己的字愣住了,脸色也不对。
“二郎,不是这个字吗?”云安推了推这人。
二郎一时不动,良晌恍然回神,却将这写了“珩”字的纸收到了袖中:“云儿,我忽然想起来学中有事,要出去一趟。”
云安觉得有些突然,但郑梦观昨日便没去太学,今天要去也不算奇怪:“好,那你就快去吧。”
二郎举动果断,又带着几分急切,很快便离了人境院。素戴送走阿春后就在廊下闲坐,忽见此状,便进来问。云安与她随口说了,并不当回事,继续歪靠着看书。
素戴一笑,不过从旁侍奉,替她收拾一地的散简,取走吃空的盘碟,不觉说道:“周燕阁自从送了那一回紫萝糕,如今便隔三差五地送,我倒不信她的心诚,莫不是敢在这吃食里动手脚吧?”
云安轻嗤,道:“她哪里有这本事,都是云夫人替她做人呢!我以为你早就看出来了。但她若要害人,还放在自己送来的东西里,也太蠢了吧?况且我这不没事么,里头连个泻药也没有。”
“好吧,算我白忖度一回。”
素戴抿了抿唇,不再多想,便要将收好的空盘送去厨下,一转身,目光无意间划过了书房的南墙。那处摆着二郎的明光铠和长剑,还有那只绣了诗句的步靫。
素戴久久停驻,默不作声反引起了云安的注意,她也顺着看去,看到了那副明光铠。“你怎么了?每回进来都要看一眼。”
原来,素戴虽不常来书房侍奉,但只要云安在,二郎都会让她替代临啸。如此多次,云安便就发现过,素戴喜欢盯着那副铠甲,似乎显得比她还上心。
素戴顿觉窘迫,脸上一红,道:“我就是觉得,总觉得步靫上的字奇怪,那字的走针绣法,好像在哪里见过的。”
云安不通针线,皱眉说道:“又不是绣花,还有什么针法吗?”
“每个人下针都有自己的习惯,就像写字的字迹,每个人都不同。”素戴说着再三望了一眼南墙,只是仍无头绪,“罢了,针法相似的也多,夫人看书吧,我去了。”
云安才没有往心里去,应了声,重新沉浸到杂书的欢乐中。
第35章 欲留芳
郑梦观离开家,却非是要到太学,带着临啸一道,主仆二人的马蹄直向悲田院驰去。临啸不解主人用意,二郎也没有明言,及至抵达悲田院门首,二郎才谨慎地问起:
“我上回遣你来此打听一个叫王行的人,你除了知道他并非悲田院主事,可有觉出别的异常?”
临啸是有一说一的老实人,又岂敢对二郎隐瞒,只连忙摇头,道:“小奴都对公子如实说了,真正的主事叫蒋融,他说自己当了快十年的主事,从未听说过叫王行的人,也没见过陌生面孔。”
这话确是二郎第二次听了,却比上回听时更让他不踏实。他从袖中取出了那张写着“珩”字的纸,展开又盯了许久——把这个字拆开,不就是“王行”两个字吗?
若非云安无意间提问申王的名讳,二郎根本想不到这样的关联。设若王行就是申王,那他以亲王之尊躲在偏狭的悲田院里与人议事,却是意欲何为?
而对二郎来说更重要的是,王行亲近云安之意昭然若揭,便自探春宴起,申王府两次来邀,这没来由的“厚爱”,是否就是王行利用申王妃的名义,所使的障眼法呢?
想到此处,二郎将“珩”字纸张猛撕成两半,握在手心,攥得骨节发白。“你带路,我要见一见蒋主事。”
二郎努力克制住胸中的躁动,还要最后探一探虚实。临啸亦不难发觉主人的情绪有变,不敢动问,即刻便引路前去。
顷刻到了悲田院官吏的值房,说明来意,便有个差役请了主事出来。二郎没见过蒋捷,就看是个绿袍的中年人,可待要开口,临啸却将他拦住了,急道:
“公子,换人了!他不是蒋主事!”
二郎登时大惊,将心里的种种猜测一下压实了□□分。
看这主仆二人举动奇怪,那官人抚须一叹,有些不耐烦:“你们是何人啊?怎么不问清楚就来找人呢?蒋主事上个月就调了外任,如今这悲田院是我孙某人做主了!”
官员调动看似平常,又是这等品阶低微的官职,更似乎是不起眼的小事。然则偏偏是这个关口,那个做了十年主事的蒋捷就一下调走了,还是外任,一时是寻不着人的。
“那孙主事可知,蒋主事调往了何处?”二郎拱手一礼,问道。
“不知不知,我与蒋主事素不相识,不过接任而已。哪里来的后生?快走吧!”这孙主事本就懒得接待,又看并不是来找他的,大手一挥转回了值房。
果然询问无果,二郎只有另作计较,但他已经认定了,这个王行不会是旁人。离了悲田院,二郎没有返家,只叫临啸先回,自己又往从前的几位同窗家拜访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