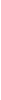除夕夜,京市秦家大宅。
老宅是前朝王府改的,檐角挂着红灯笼,廊下点着宫灯,朱漆大门前停满了挂着各式特殊牌照的黑色轿车。
宅子里暖气开得足,空气里弥漫着佛手柑的自然熏香和上等食材煨出来的肉香,庭院里簌簌飘落白雪。
麻将房里传来二房几个婶子伯母的说笑和搓牌声,秦玉桐和几个未成年小孩坐在黄花梨木的长桌边,正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
“哎呦,我们桐桐真是越长越漂亮了,这皮肤,跟剥了壳的鸡蛋似的,快让二婶看看。”
二婶说着,就从爱马仕的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红包,不由分说地塞进秦玉桐手里,“拿着,二婶给的压岁钱。以前你在外面,二婶也没机会给你,今年可得补上。”
“就是就是,叁叔也给你准备了。”叁叔叁十多看起来四十多了,大腹便便,笑起来脸都是褶子。
可能是军队伙食好吧,她一想起上次把顾廷邺认错就想脚趾扣地。
希望他贵人多忘事,谁让他长得也不像二十多的人。
秦玉桐垂着眸,看着手里那几个烫金的“福”字,指尖能清晰地感觉到里面厚厚一沓崭新纸币的棱角。
她当然知道,这些人不是在弥补什么“以前”。
不过是因为,秦奕洲如今是京市检察院最年轻的副检察长,是秦家这一辈里,走得最高最稳的那个。
他们巴结不上秦奕洲,便来讨好她这个他放在心尖上的养女。
“谢谢二婶,谢谢叁叔。”她弯起眼睛,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甜美笑容,声音乖巧。
应付完一圈,又打发围着她的一圈小孩子,她像只羽翼华丽的小鸟,飞回了秦奕洲身边。
男人刚从书房出来,换下了一身笔挺的检察官制服,穿着件深灰色的羊绒衫,金丝眼镜的镜片上氤氲着饭厅里的暖气,显得那双狭长的狐狸眼愈发深邃柔和。他正跟二叔低声说着什么,看见她过来,便自然地停了话头。
“二叔。”秦玉桐朝秦奕贤点了点头。
秦奕贤也是一双秦家人的招牌狐狸眼,朝她温和笑了笑。
秦玉桐仰起脸,献宝似的将手里几乎捧不住的一沓红包递到秦奕洲面前,尾音拖得长长的,带点炫耀的骄矜:“爸爸,你看。”
秦奕洲抬手,温热的指腹擦过她冻得有些凉的脸颊,将她一缕滑落的碎发别到耳后。
“我的小乖收了这么多压岁钱?”他低声笑着,声音像醇厚的红酒。
“才不是呢,”秦玉桐撇了撇嘴,小声抱怨,“都是看你面子才给我的。”
她一双漂亮的眼睛亮晶晶地瞅着他,里面的期待毫不掩饰:“爸爸你的呢?你给我准备了什么?”
明明都十八岁了,还跟小时候似的。
秦奕洲没说话,只是牵起她的手,将她带到人少的偏厅。
他从口袋里拿出的不是红包,而是一把钥匙。
他将那把冰凉的钥匙放进她温热的掌心,“保时捷911,等你拿了驾照就可以开了。”
明明前不久才送了房,现在又送这么贵的车,他这么多年的工资够吗?
都给她了,那他怎么办。
“爸爸……”小眼神可怜得紧。
男人觉得好笑,又觉得暖心,摸摸她的头,说他母亲给他留了一些遗产,让她别担心。
“小乖,”他握着她的手,将钥匙连同他的体温一起裹紧,“新年快乐。”
——
晚饭后,秦玉桐寻了个借口,独自溜达到后花园。
偌大的园子里空无一人,只有风灯在风雪中摇曳,将光影投在厚厚的积雪上。
天不知什么时候又开始下雪了。
细小的雪粒子变成鹅毛般的大片,纷纷扬扬,落了她满头满肩。
手机在羽绒服口袋里震动了一下。
她拿出来,屏幕上是一个没有存名字的香港号码。
但她知道是谁。
指尖划开接听键,一道低沉醇厚的男声透过听筒传来,像大提琴在耳边共振。
“新年好。”
秦玉桐忍不住笑起来,她用脸颊贴着冰凉的屏幕,轻声说:“商先生,你怎么知道我在等你电话?”
那边轻笑了一声,性感又迷人:“是吗?我还以为秦小姐已经将我忘了。”
“才没有。”她还记得答应他今晚打电话。
她呼出的热气在空气中凝成一团白雾,“我这里下雪了,好大。”
这话说得像个跟大人分享新奇玩具的小朋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香港上一次下雪还是在1975年,可以说他从出生起就没在香港见过雪。
“拍张相片给我看。”他说。
只拍雪么。她想不是的。
秦玉桐咬着唇,点开相机,切换到自拍模式。
屏幕里的女孩,脸颊被冻得泛起一层健康的粉,鼻尖红红的,依旧小巧精致。黑色的长发上沾着星星点点的雪花,衬得一双眼睛像浸在水里的黑曜石,棋子般分明。
背景是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红墙白雪,意境绝美。
她挑挑拣拣,删了好几张,才找到一张最满意的。
那张照片里,少女微微仰着头,闭着眼,睫毛上落着一片将融未融的雪花,唇角却微微翘着,像在感受一个温柔的亲吻。
点击,发送。
“收到了吗?”她问。
“收到了。”商屿的声音里带了点笑意,“很靓。”
就这两个字,秦玉桐的耳朵尖却不争气地红了。
明明每天都被夸了,没道理因为这一句就害羞吧
真没出息。她唾弃自己。
她靠在冰冷的朱红廊柱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着。
聊他在香港的年夜饭吃了什么,聊她剧组里的八卦,聊杨导又在片场骂了谁……都是些不成调的废话,可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好像都变得有趣起来。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直到她的手脚都冻得有些麻了,才后知后觉地挂了电话。
她将手机揣回兜里,脸上的笑意还没散去,转身准备回屋。
一抬眼,却看见秦奕洲就站在不远处的廊下。
他不知在那儿站了多久,身上只穿着那件薄薄的羊绒衫,金丝眼镜后的那双狐狸眼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晦暗不明。
雪花落在他肩上,积了薄薄的一层,他也没拂去。
秦玉桐的笑容僵在脸上,底气不足。
“……爸爸?”
秦奕洲朝她走过来,步子不疾不徐。
他的手指碰到她冰凉的脸颊,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
“跟谁打电话?”
声音平静无波,听不出喜怒。
“能聊这么久。”
老宅是前朝王府改的,檐角挂着红灯笼,廊下点着宫灯,朱漆大门前停满了挂着各式特殊牌照的黑色轿车。
宅子里暖气开得足,空气里弥漫着佛手柑的自然熏香和上等食材煨出来的肉香,庭院里簌簌飘落白雪。
麻将房里传来二房几个婶子伯母的说笑和搓牌声,秦玉桐和几个未成年小孩坐在黄花梨木的长桌边,正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
“哎呦,我们桐桐真是越长越漂亮了,这皮肤,跟剥了壳的鸡蛋似的,快让二婶看看。”
二婶说着,就从爱马仕的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红包,不由分说地塞进秦玉桐手里,“拿着,二婶给的压岁钱。以前你在外面,二婶也没机会给你,今年可得补上。”
“就是就是,叁叔也给你准备了。”叁叔叁十多看起来四十多了,大腹便便,笑起来脸都是褶子。
可能是军队伙食好吧,她一想起上次把顾廷邺认错就想脚趾扣地。
希望他贵人多忘事,谁让他长得也不像二十多的人。
秦玉桐垂着眸,看着手里那几个烫金的“福”字,指尖能清晰地感觉到里面厚厚一沓崭新纸币的棱角。
她当然知道,这些人不是在弥补什么“以前”。
不过是因为,秦奕洲如今是京市检察院最年轻的副检察长,是秦家这一辈里,走得最高最稳的那个。
他们巴结不上秦奕洲,便来讨好她这个他放在心尖上的养女。
“谢谢二婶,谢谢叁叔。”她弯起眼睛,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甜美笑容,声音乖巧。
应付完一圈,又打发围着她的一圈小孩子,她像只羽翼华丽的小鸟,飞回了秦奕洲身边。
男人刚从书房出来,换下了一身笔挺的检察官制服,穿着件深灰色的羊绒衫,金丝眼镜的镜片上氤氲着饭厅里的暖气,显得那双狭长的狐狸眼愈发深邃柔和。他正跟二叔低声说着什么,看见她过来,便自然地停了话头。
“二叔。”秦玉桐朝秦奕贤点了点头。
秦奕贤也是一双秦家人的招牌狐狸眼,朝她温和笑了笑。
秦玉桐仰起脸,献宝似的将手里几乎捧不住的一沓红包递到秦奕洲面前,尾音拖得长长的,带点炫耀的骄矜:“爸爸,你看。”
秦奕洲抬手,温热的指腹擦过她冻得有些凉的脸颊,将她一缕滑落的碎发别到耳后。
“我的小乖收了这么多压岁钱?”他低声笑着,声音像醇厚的红酒。
“才不是呢,”秦玉桐撇了撇嘴,小声抱怨,“都是看你面子才给我的。”
她一双漂亮的眼睛亮晶晶地瞅着他,里面的期待毫不掩饰:“爸爸你的呢?你给我准备了什么?”
明明都十八岁了,还跟小时候似的。
秦奕洲没说话,只是牵起她的手,将她带到人少的偏厅。
他从口袋里拿出的不是红包,而是一把钥匙。
他将那把冰凉的钥匙放进她温热的掌心,“保时捷911,等你拿了驾照就可以开了。”
明明前不久才送了房,现在又送这么贵的车,他这么多年的工资够吗?
都给她了,那他怎么办。
“爸爸……”小眼神可怜得紧。
男人觉得好笑,又觉得暖心,摸摸她的头,说他母亲给他留了一些遗产,让她别担心。
“小乖,”他握着她的手,将钥匙连同他的体温一起裹紧,“新年快乐。”
——
晚饭后,秦玉桐寻了个借口,独自溜达到后花园。
偌大的园子里空无一人,只有风灯在风雪中摇曳,将光影投在厚厚的积雪上。
天不知什么时候又开始下雪了。
细小的雪粒子变成鹅毛般的大片,纷纷扬扬,落了她满头满肩。
手机在羽绒服口袋里震动了一下。
她拿出来,屏幕上是一个没有存名字的香港号码。
但她知道是谁。
指尖划开接听键,一道低沉醇厚的男声透过听筒传来,像大提琴在耳边共振。
“新年好。”
秦玉桐忍不住笑起来,她用脸颊贴着冰凉的屏幕,轻声说:“商先生,你怎么知道我在等你电话?”
那边轻笑了一声,性感又迷人:“是吗?我还以为秦小姐已经将我忘了。”
“才没有。”她还记得答应他今晚打电话。
她呼出的热气在空气中凝成一团白雾,“我这里下雪了,好大。”
这话说得像个跟大人分享新奇玩具的小朋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香港上一次下雪还是在1975年,可以说他从出生起就没在香港见过雪。
“拍张相片给我看。”他说。
只拍雪么。她想不是的。
秦玉桐咬着唇,点开相机,切换到自拍模式。
屏幕里的女孩,脸颊被冻得泛起一层健康的粉,鼻尖红红的,依旧小巧精致。黑色的长发上沾着星星点点的雪花,衬得一双眼睛像浸在水里的黑曜石,棋子般分明。
背景是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红墙白雪,意境绝美。
她挑挑拣拣,删了好几张,才找到一张最满意的。
那张照片里,少女微微仰着头,闭着眼,睫毛上落着一片将融未融的雪花,唇角却微微翘着,像在感受一个温柔的亲吻。
点击,发送。
“收到了吗?”她问。
“收到了。”商屿的声音里带了点笑意,“很靓。”
就这两个字,秦玉桐的耳朵尖却不争气地红了。
明明每天都被夸了,没道理因为这一句就害羞吧
真没出息。她唾弃自己。
她靠在冰冷的朱红廊柱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着。
聊他在香港的年夜饭吃了什么,聊她剧组里的八卦,聊杨导又在片场骂了谁……都是些不成调的废话,可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好像都变得有趣起来。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直到她的手脚都冻得有些麻了,才后知后觉地挂了电话。
她将手机揣回兜里,脸上的笑意还没散去,转身准备回屋。
一抬眼,却看见秦奕洲就站在不远处的廊下。
他不知在那儿站了多久,身上只穿着那件薄薄的羊绒衫,金丝眼镜后的那双狐狸眼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晦暗不明。
雪花落在他肩上,积了薄薄的一层,他也没拂去。
秦玉桐的笑容僵在脸上,底气不足。
“……爸爸?”
秦奕洲朝她走过来,步子不疾不徐。
他的手指碰到她冰凉的脸颊,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
“跟谁打电话?”
声音平静无波,听不出喜怒。
“能聊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