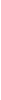第38章尘封之处
正午的阳光透过厚重的窗帘缝隙,在尘封的房间里切割出几道金色的光带。
沉昭掀开家具罩布的瞬间,陈年的灰尘在光束中飞舞,像一场微型暴风雪。萧野猛地别过脸,红发下的鼻尖皱起,硬生生把喷嚏憋成了几声闷咳。
是那个男孩的房间。萧野的声音带着奇怪的鼻音,手指拂过书架上褪色的童话书。那些精装本的烫金标题已经斑驳,夹杂着几本《解剖学图谱》和《神经医学基础》,书脊的磨损程度不一。
“男孩的房间?”沉昭的指尖停在半空,她对这个房间毫无印象。
就是我们附身的那个...萧野突然顿住,喉结滚动了一下,你当时...不是他?
我附身的是艾德琳。
第二幕前的记忆碎片突然涌上来,丝绸床单的触感,交织的呼吸,还有修长手指抚过后颈的战栗。
灼热的回忆让萧野耳尖温度飙升,他猛地转身假装研究书柜,却撞得几本书哗啦作响。
…艾德琳和男孩曾经发生关系…那四舍五入…他和沉昭是不是…咳咳…
这些事对他来说过于超前,毕竟,他连初吻都还留着。
鲜少有正经女孩愿意同他交好,萧野既不愿意去泡吧猎艳,也不愿意学其他同伴用暴力开始并维持一段关系。
每次训练结束同伴们邀请他去夜店时,他都会拒绝,然后回被窝继续做着会遇见她的梦。
等待沉昭看上他,来找他,开启一段入室抢劫般的爱情。
沉昭完全没注意到同伴的异常。她的注意力被书桌上的乐谱吸引,泛黄的纸页上,《安魂曲》的片段被稚嫩的笔迹反复抄写,某些音符被铅笔涂改得几乎穿透纸背。
她在心里冷静分析:如果这里是公爵小时候的房间,他为什么要封存起来?
如果单纯作为储物间,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除非这里放着不能被他人所见,而公爵本人又无法舍弃的事物。隐秘到不能被仆从触碰。
衣柜里挂着几套小号贵族礼服,面料考究却款式朴素。沉昭检查内袋时,一把黄铜钥匙悄然落入掌心,带着经年累月的金属凉意。
“沉昭,这里锁上了。”萧野呼唤她。
沉昭过去查看,书桌抽屉的锁孔已经氧化,是如出一辙的黄铜材质,幸好钥匙依然能顺滑插入。随着咔嗒轻响,陈年的墨水味扑面而来。
抽屉内,日记本的皮革封面布满细纹,下面压着另一把造型古怪的铁钥匙,以及装在丝绸小袋里,漆黑如墨,却在阳光下泛着诡异的金属光泽的种子。
看着像黑蔷薇种子。萧野凑过来,红发扫过沉昭的耳侧带着痒意。
第一本日记的羊皮封面泛着柔和的米色,第一页上的Lux字样已经有些模糊。稚嫩的笔迹记录着一个病弱男孩的孤独,他的生命几度垂危依靠母亲的祈祷堪堪维持。他的父亲永远在书房会见那些戴着面具的客人,后花园的马车时常在深夜运来蒙着白布的货物。小公爵曾偷偷掀开过一角,却只看到少女苍白的指尖和亚麻色的长发。当他鼓起勇气询问父亲时,得到的永远是谩骂和耳光。
这些碎片与第一幕的剧情基本吻合。
第二本日记用的是朴素的牛皮封面,内页的笔迹已经变得锋利。少年公爵的身体像他的希望一样日渐衰弱,他请来的家庭教师换了一茬又一茬,他有时祈求神明再次治愈他的身体,有时又哀怨自己不该出生。某页发皱的纸上写着:今天又看到父亲的情妇从温室出来...母亲身上的伤痕增加了,即使隔着门我也能听到他们的争吵...为什么我不能带她逃离…
墨迹在这里晕开一大片,像是被泪水打湿过。
第三本日记的黑色封皮已经皲裂,如同主人濒临崩溃的精神状态。成年的公爵字迹狂乱,有些页面上还沾着可疑的暗渍:沐浴圣水根本没用…医生说我活不过这个冬天...艾德琳又来劝我放弃...那些贱民凭什么拥有健康的身体?!最新的一页上,笔迹突然变得异常工整:我找到了,术法是真的。我会活下去,哪怕要献祭所有人。
沉昭的指尖轻轻抚过最后那段文字,思绪飘忽。她将抽屉里那把造型古怪的钥匙收进系统背包,金属入手的瞬间,耳边似乎响起一声遥远的叹息。
两人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房间里再没有其他值得注意的,都是一些贵族公子家的小玩意。
他们故伎重施,来到相邻房间的阳台上。
下午的斜阳为东翼阳台镀上一层金色。沉昭的指尖刚触到玻璃窗,后面厚重的窗帘突然被猛地拉开。
玻璃后是艾德琳苍白的脸,她幽深的瞳孔在暮色中泛着诡异的光。她推开落地窗,萧野和沉昭走进屋内,下一刻红发男人手中的军刺已经抵在贵妇的咽喉处。
我以为剪断黑蔷薇你就自由了。沉昭的声音比刀锋更冷。
聪明的女士...艾德琳的嘴角扭曲成一个诡异的角度,仿佛愤怒但又出于礼节不得不微笑。
指尖轻抚着腰间的黑蔷薇,她的声音变得压抑:我也这么以为。但他要我偿还。
公爵?你见到他了?沉昭不抱希望地随口发问,环视房间一圈,干净得和其他客房没区别。
不。艾德琳的瞳孔微微扩散,她按住自己胸口,我们彼此连心,同我愤恨他般,他也也厌弃着我…我能听见他的声音…
“这和我们无关。萧野,走了。”沉昭打断她不知所谓的话,没有信息,她不想浪费时间,转身就要离开。
“直接走吗?”萧野在阴影里发出疑问,红发透着张扬的气质,军刺始终没有放下。
等等!艾德琳上前抓住沉昭的手腕,冰凉的触感不似活人,我能带你们找到他。
夫人?门外突然响起机械的敲门声,隔壁房间的窗户被破坏了,您是否看到可疑人物?
沉昭猛地甩开她的手,却见艾德琳快一步已经挡在门前,两人无声对峙,双方都寸步不让。
萧野在一边看着,如非必要,他不想对女性动手。
留下来。艾德琳的唇形无声地说道。
沉昭额头青筋暴起,忍着杀人的冲动,咬着牙问道:“你打算卖我们第二次?”
“相信我。”
钥匙转动的声音清晰可闻,衣柜门被拉开,里面挂满的华服散发出浓郁的玫瑰香味。
沉昭与萧野被迫挤进这个逼仄的空间,丝绸面料摩擦发出窸窣声响。萧野的呼吸喷在她后颈,滚烫得惊人。
侍从打开门时,房间内只剩下艾德琳一人。
我在换衣服。艾德琳的声音冷淡,伴随着衣料滑落的沙沙声。
侍从的陶瓷眼球转动时发出齿轮声:公爵吩咐要确保您的安全...
我说,我没事!像是被触及了逆鳞,暴怒的艾德琳抄起化妆镜前的花瓶向侍从扔去,“滚出去!”
花瓶碎裂的声响震得衣柜微微颤动。透过缝隙,沉昭看到侍从面无表情地拾起碎片,瓷白的脸上还沾着水珠。
狭窄的衣柜内,萧野的胸膛与沉昭紧贴。透过单薄的侍从制服,他能清晰地感受到对方身体的温度和曲线。沉昭的发丝扫过他鼻尖,带着若有若无的血腥味与冷香。他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目光落在她低垂的睫毛上,这个角度她的锋芒不再毕露,反而像一个普通的女生。
那个普通的女生抬眼,棕色瞳仁倒映出他自己的脸庞,像是一个无法脱身的漩涡朝他靠近。
看什么这么入迷?带笑的气音突然钻入耳蜗,萧野这才惊觉自己竟看失了神。
他慌乱别开脸,却因空间所限只能徒劳地后仰,后脑勺咚地撞上衣柜内板。
反正不是看你...他声音发紧,想推开又无处着手,最终只能死死抓住身后的衣架。木架不堪重负的吱呀声在密闭空间里格外清晰。
咔嗒——衣柜门突然洞开,艾德琳倚在门边,苍白的脸上挂着促狭的笑:我这里有现成的床铺,两位需要借用吗?
沉昭利落地挤出衣柜,顺手理了理凌乱的衣领:不必了,留给你和'那位'享用。她意有所指地瞥向艾德琳腰上枯萎的黑蔷薇。
萧野几乎是跌出衣柜的,红发下的耳尖红得滴血。他粗声粗气地转移话题:你说要帮我们找到公爵,怎么帮?公馆快被我们翻遍了,连个鬼影都没见着。
艾德琳的表情突然阴沉下来,缓慢走到床头拿起那朵唯一的黑蔷薇:公爵大慨不是不想露面...
她声音渐低,而是即使露了,你们也不知道那是他。
我给你们情报,你们帮我归还黑蔷薇…她伸出苍白的手,成交?
——
沉昭掀开家具罩布的瞬间,陈年的灰尘在光束中飞舞,像一场微型暴风雪。萧野猛地别过脸,红发下的鼻尖皱起,硬生生把喷嚏憋成了几声闷咳。
是那个男孩的房间。萧野的声音带着奇怪的鼻音,手指拂过书架上褪色的童话书。那些精装本的烫金标题已经斑驳,夹杂着几本《解剖学图谱》和《神经医学基础》,书脊的磨损程度不一。
“男孩的房间?”沉昭的指尖停在半空,她对这个房间毫无印象。
就是我们附身的那个...萧野突然顿住,喉结滚动了一下,你当时...不是他?
我附身的是艾德琳。
第二幕前的记忆碎片突然涌上来,丝绸床单的触感,交织的呼吸,还有修长手指抚过后颈的战栗。
灼热的回忆让萧野耳尖温度飙升,他猛地转身假装研究书柜,却撞得几本书哗啦作响。
…艾德琳和男孩曾经发生关系…那四舍五入…他和沉昭是不是…咳咳…
这些事对他来说过于超前,毕竟,他连初吻都还留着。
鲜少有正经女孩愿意同他交好,萧野既不愿意去泡吧猎艳,也不愿意学其他同伴用暴力开始并维持一段关系。
每次训练结束同伴们邀请他去夜店时,他都会拒绝,然后回被窝继续做着会遇见她的梦。
等待沉昭看上他,来找他,开启一段入室抢劫般的爱情。
沉昭完全没注意到同伴的异常。她的注意力被书桌上的乐谱吸引,泛黄的纸页上,《安魂曲》的片段被稚嫩的笔迹反复抄写,某些音符被铅笔涂改得几乎穿透纸背。
她在心里冷静分析:如果这里是公爵小时候的房间,他为什么要封存起来?
如果单纯作为储物间,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除非这里放着不能被他人所见,而公爵本人又无法舍弃的事物。隐秘到不能被仆从触碰。
衣柜里挂着几套小号贵族礼服,面料考究却款式朴素。沉昭检查内袋时,一把黄铜钥匙悄然落入掌心,带着经年累月的金属凉意。
“沉昭,这里锁上了。”萧野呼唤她。
沉昭过去查看,书桌抽屉的锁孔已经氧化,是如出一辙的黄铜材质,幸好钥匙依然能顺滑插入。随着咔嗒轻响,陈年的墨水味扑面而来。
抽屉内,日记本的皮革封面布满细纹,下面压着另一把造型古怪的铁钥匙,以及装在丝绸小袋里,漆黑如墨,却在阳光下泛着诡异的金属光泽的种子。
看着像黑蔷薇种子。萧野凑过来,红发扫过沉昭的耳侧带着痒意。
第一本日记的羊皮封面泛着柔和的米色,第一页上的Lux字样已经有些模糊。稚嫩的笔迹记录着一个病弱男孩的孤独,他的生命几度垂危依靠母亲的祈祷堪堪维持。他的父亲永远在书房会见那些戴着面具的客人,后花园的马车时常在深夜运来蒙着白布的货物。小公爵曾偷偷掀开过一角,却只看到少女苍白的指尖和亚麻色的长发。当他鼓起勇气询问父亲时,得到的永远是谩骂和耳光。
这些碎片与第一幕的剧情基本吻合。
第二本日记用的是朴素的牛皮封面,内页的笔迹已经变得锋利。少年公爵的身体像他的希望一样日渐衰弱,他请来的家庭教师换了一茬又一茬,他有时祈求神明再次治愈他的身体,有时又哀怨自己不该出生。某页发皱的纸上写着:今天又看到父亲的情妇从温室出来...母亲身上的伤痕增加了,即使隔着门我也能听到他们的争吵...为什么我不能带她逃离…
墨迹在这里晕开一大片,像是被泪水打湿过。
第三本日记的黑色封皮已经皲裂,如同主人濒临崩溃的精神状态。成年的公爵字迹狂乱,有些页面上还沾着可疑的暗渍:沐浴圣水根本没用…医生说我活不过这个冬天...艾德琳又来劝我放弃...那些贱民凭什么拥有健康的身体?!最新的一页上,笔迹突然变得异常工整:我找到了,术法是真的。我会活下去,哪怕要献祭所有人。
沉昭的指尖轻轻抚过最后那段文字,思绪飘忽。她将抽屉里那把造型古怪的钥匙收进系统背包,金属入手的瞬间,耳边似乎响起一声遥远的叹息。
两人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房间里再没有其他值得注意的,都是一些贵族公子家的小玩意。
他们故伎重施,来到相邻房间的阳台上。
下午的斜阳为东翼阳台镀上一层金色。沉昭的指尖刚触到玻璃窗,后面厚重的窗帘突然被猛地拉开。
玻璃后是艾德琳苍白的脸,她幽深的瞳孔在暮色中泛着诡异的光。她推开落地窗,萧野和沉昭走进屋内,下一刻红发男人手中的军刺已经抵在贵妇的咽喉处。
我以为剪断黑蔷薇你就自由了。沉昭的声音比刀锋更冷。
聪明的女士...艾德琳的嘴角扭曲成一个诡异的角度,仿佛愤怒但又出于礼节不得不微笑。
指尖轻抚着腰间的黑蔷薇,她的声音变得压抑:我也这么以为。但他要我偿还。
公爵?你见到他了?沉昭不抱希望地随口发问,环视房间一圈,干净得和其他客房没区别。
不。艾德琳的瞳孔微微扩散,她按住自己胸口,我们彼此连心,同我愤恨他般,他也也厌弃着我…我能听见他的声音…
“这和我们无关。萧野,走了。”沉昭打断她不知所谓的话,没有信息,她不想浪费时间,转身就要离开。
“直接走吗?”萧野在阴影里发出疑问,红发透着张扬的气质,军刺始终没有放下。
等等!艾德琳上前抓住沉昭的手腕,冰凉的触感不似活人,我能带你们找到他。
夫人?门外突然响起机械的敲门声,隔壁房间的窗户被破坏了,您是否看到可疑人物?
沉昭猛地甩开她的手,却见艾德琳快一步已经挡在门前,两人无声对峙,双方都寸步不让。
萧野在一边看着,如非必要,他不想对女性动手。
留下来。艾德琳的唇形无声地说道。
沉昭额头青筋暴起,忍着杀人的冲动,咬着牙问道:“你打算卖我们第二次?”
“相信我。”
钥匙转动的声音清晰可闻,衣柜门被拉开,里面挂满的华服散发出浓郁的玫瑰香味。
沉昭与萧野被迫挤进这个逼仄的空间,丝绸面料摩擦发出窸窣声响。萧野的呼吸喷在她后颈,滚烫得惊人。
侍从打开门时,房间内只剩下艾德琳一人。
我在换衣服。艾德琳的声音冷淡,伴随着衣料滑落的沙沙声。
侍从的陶瓷眼球转动时发出齿轮声:公爵吩咐要确保您的安全...
我说,我没事!像是被触及了逆鳞,暴怒的艾德琳抄起化妆镜前的花瓶向侍从扔去,“滚出去!”
花瓶碎裂的声响震得衣柜微微颤动。透过缝隙,沉昭看到侍从面无表情地拾起碎片,瓷白的脸上还沾着水珠。
狭窄的衣柜内,萧野的胸膛与沉昭紧贴。透过单薄的侍从制服,他能清晰地感受到对方身体的温度和曲线。沉昭的发丝扫过他鼻尖,带着若有若无的血腥味与冷香。他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目光落在她低垂的睫毛上,这个角度她的锋芒不再毕露,反而像一个普通的女生。
那个普通的女生抬眼,棕色瞳仁倒映出他自己的脸庞,像是一个无法脱身的漩涡朝他靠近。
看什么这么入迷?带笑的气音突然钻入耳蜗,萧野这才惊觉自己竟看失了神。
他慌乱别开脸,却因空间所限只能徒劳地后仰,后脑勺咚地撞上衣柜内板。
反正不是看你...他声音发紧,想推开又无处着手,最终只能死死抓住身后的衣架。木架不堪重负的吱呀声在密闭空间里格外清晰。
咔嗒——衣柜门突然洞开,艾德琳倚在门边,苍白的脸上挂着促狭的笑:我这里有现成的床铺,两位需要借用吗?
沉昭利落地挤出衣柜,顺手理了理凌乱的衣领:不必了,留给你和'那位'享用。她意有所指地瞥向艾德琳腰上枯萎的黑蔷薇。
萧野几乎是跌出衣柜的,红发下的耳尖红得滴血。他粗声粗气地转移话题:你说要帮我们找到公爵,怎么帮?公馆快被我们翻遍了,连个鬼影都没见着。
艾德琳的表情突然阴沉下来,缓慢走到床头拿起那朵唯一的黑蔷薇:公爵大慨不是不想露面...
她声音渐低,而是即使露了,你们也不知道那是他。
我给你们情报,你们帮我归还黑蔷薇…她伸出苍白的手,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