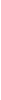十月初已经入冬,前几日刚下过一场薄雪,路旁的林木上只稀稀拉拉挂着几片干黄的树叶。
此刻,溶月正晃晃悠悠坐在马车里,伏在马车车窗处往外头望了一会,然后便放下布帘,轻叹了句“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
外头虽然十月寒风袭人,她坐在车厢里头,手里捧着一只银鎏金暖手炉,车厢里还放着个炭火盆,便是冬日也丝毫不觉得冷。
这路是去昌乐的,前些日日姜家送来了帖子,簪花宴本来定在九月下旬,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又改在十月初五。
徐弘川本来不许她回去,她其实也不想回去,现如今她早就把徐府当成了自己的家。可名义上她还是姜家儿媳,若是不回去难免惹人非议,再给他招来什么麻烦,她心里过意不去。
溶月摩挲着精致温热的暖炉,想起昨夜春宵帐暖时,两人耳鬓厮磨,那浑人一边掐着她的腰肢一边从后头入进来,还贴着她的耳根调戏她:“弟妹回去,可别见着了夫君就忘了大伯……”说完就发狠顶进她的腿心,花芯叫他捅得酥烂!
她红着脸腹诽,两人欢爱时,那浑人还动不动地就让她唤他“大伯”!
这个不要脸的,每次她乖乖叫了“大伯”,他反而肏得更凶……
两人终究是伯媳,姜文诚才是她正经夫君。每每想到此处,溶月都面带愁容,忍不住轻轻叹气。
她要如何光明正大地同徐弘川在一起?
好似比登天还难……
溶月轻轻摸着自己的肚子,忍不住疑惑她为何至今还未有孕。
徐弘川只要是在府中,恨不得夜夜春宵,难道……是她身子有什么隐疾?
可是先前昌乐的范郎中给她切过脉,说她并无大碍,范郎中的医术高明,应该不会出错啊。
溶月突然想起,徐弘川有时候好像……没弄在里头……最后都是喷在她的肚皮或是屁股上……
她轻轻皱了皱眉,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他为什么会弄在外面,难道他不想让自己有孕?
溶月又按了按自己的肚腹,突然又笑了笑,暗道可能是她想多了。
她与他欢好,十回有八回不是被弄昏过去,就是脑中晕呼呼的,根本不晓得他是弄在里头还是外头,她瞧见的那几回应该也做不得数。
不过,等她这次从姜家回来,还是去找五爷看看,是不是她身子出了什么岔子。
到了姜家后,张虎前去叫门。
这次姜家办簪花宴,徐弘川让张虎和周实山陪她回来,也算代替他露个面、全了礼数。
徐弘川同她说,姜家那一家子的薄情寡义,他本来是懒得理会,绝不可能给他们这个脸!
为了免去落人话柄,就让张虎和周实山带了份礼来姜家,就算有所交代了。
吴管家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恭恭敬敬地将三人迎了进去。
他们刚进前院,溶月远远地便瞧见她公婆和夫君已经等在前厅那里,见了她全都愣住,好似不认得她一样,反复上下打量了一番,又瞧见徐弘川没来,脸上难掩失望的神色。
溶月跟着陈氏往内院走去,姜元发和姜文诚则笑眯眯地把张虎和周实山迎入正厅招待。
陈氏眼红地打量着溶月一身华贵的装扮,她身上罩着石青色锦缎狐裘,里头是桃红色百蝶戏牡丹妆花缎大袖袄,下着湖绿色缠枝宝相花马面裙,一身袄裙领口、袖口和裙边都镶着一圈紫貂皮边,头上更是珠翠堆满,件件钗簪都镶着宝石,做工更是精致!
真是人要衣装,从前低眉顺眼的儿媳,如今尊贵又气派,活像个贵夫人!
陈氏脸上的笑是硬挤出来的,实际上快咬碎了一口牙,嫉妒得双眼发红,无法想象徐弘川府中是如何富贵泼天,瞧溶月头上戴的,身上穿的,都是她连见都没见过的好东西!
这小蹄子看来是得了宠了,那小畜生竟舍得给她穿这样名贵的衣裳!
陈氏领着溶月直接去了自己屋,待她脱下大氅、给自己行了礼后,又挤出个笑来,指着桌上堆着的四五个锦盒说道:“今日簪花宴,你两个舅父也来了,毕竟是姜家的大事。这是你两个舅父专门给你的,你在徐府当差,是姜家的功臣,姜家阖家老小都指望着你呢。”
溶月静静地听着婆母的话,轻轻瞥了一眼那几只锦盒,只是挺直了腰身却并未答话。
如今她站在陈氏面前,面对陈氏那张刻薄丑陋的脸庞,虽然心里头是说不出的憎恶,但却再无从前的忐忑和惧怕。
连她自己都讶异于这种变化,她从未想过有一天她能不卑不亢地平视她这位婆母,不必做小伏低、低眉顺眼!
陈氏见溶月一副云淡风轻的姿态,双眼沉着淡然,心里倒生出几分忐忑来。
果真是徐府待久了,还真是装得像个贵人!
陈氏尴尬地轻咳一声,扶着圈椅的扶手坐了下来,示意赵嬷嬷把锦盒打开,然后又接着说道:“这是两只福字纹金镯,一副如意云纹金项圈,还有两支石榴松鼠金步摇。哦对了,你两个舅父还拿了几匹缎子给你,我瞧着那花色好,便拿去做了几身衣裳。”
溶月只随意瞥了一眼那几件首饰,如今在徐府见多了名贵器物,那几件东西瞧着分量不少,做工却粗糙,连红杏头上戴的金钗都比那几个好看些。
她心中暗自冷笑,她这个婆母平日一毛不拔,她娘家兄弟送礼给她,想必是与徐弘川有关。
她平静地答道:“媳妇无功不受禄,不敢收两位舅父的礼。”
陈氏见她推脱,干笑两声:“你这孩子还客气什么,舅父给你的你就拿着,都是自家人。”
溶月腰杆挺得笔直,并没有收下的意思,也不搭话,明摆着态度冷淡,陈氏心里突然一沉,不悦地眯起三角眼。
几日不见,果然是仗了那小畜生的势,在她面前都敢拿乔了!
作者:
我们溶宝如今可是有靠山了吼吼~~~~~~~
背靠大树好乘凉~~~~~
此刻,溶月正晃晃悠悠坐在马车里,伏在马车车窗处往外头望了一会,然后便放下布帘,轻叹了句“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
外头虽然十月寒风袭人,她坐在车厢里头,手里捧着一只银鎏金暖手炉,车厢里还放着个炭火盆,便是冬日也丝毫不觉得冷。
这路是去昌乐的,前些日日姜家送来了帖子,簪花宴本来定在九月下旬,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又改在十月初五。
徐弘川本来不许她回去,她其实也不想回去,现如今她早就把徐府当成了自己的家。可名义上她还是姜家儿媳,若是不回去难免惹人非议,再给他招来什么麻烦,她心里过意不去。
溶月摩挲着精致温热的暖炉,想起昨夜春宵帐暖时,两人耳鬓厮磨,那浑人一边掐着她的腰肢一边从后头入进来,还贴着她的耳根调戏她:“弟妹回去,可别见着了夫君就忘了大伯……”说完就发狠顶进她的腿心,花芯叫他捅得酥烂!
她红着脸腹诽,两人欢爱时,那浑人还动不动地就让她唤他“大伯”!
这个不要脸的,每次她乖乖叫了“大伯”,他反而肏得更凶……
两人终究是伯媳,姜文诚才是她正经夫君。每每想到此处,溶月都面带愁容,忍不住轻轻叹气。
她要如何光明正大地同徐弘川在一起?
好似比登天还难……
溶月轻轻摸着自己的肚子,忍不住疑惑她为何至今还未有孕。
徐弘川只要是在府中,恨不得夜夜春宵,难道……是她身子有什么隐疾?
可是先前昌乐的范郎中给她切过脉,说她并无大碍,范郎中的医术高明,应该不会出错啊。
溶月突然想起,徐弘川有时候好像……没弄在里头……最后都是喷在她的肚皮或是屁股上……
她轻轻皱了皱眉,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他为什么会弄在外面,难道他不想让自己有孕?
溶月又按了按自己的肚腹,突然又笑了笑,暗道可能是她想多了。
她与他欢好,十回有八回不是被弄昏过去,就是脑中晕呼呼的,根本不晓得他是弄在里头还是外头,她瞧见的那几回应该也做不得数。
不过,等她这次从姜家回来,还是去找五爷看看,是不是她身子出了什么岔子。
到了姜家后,张虎前去叫门。
这次姜家办簪花宴,徐弘川让张虎和周实山陪她回来,也算代替他露个面、全了礼数。
徐弘川同她说,姜家那一家子的薄情寡义,他本来是懒得理会,绝不可能给他们这个脸!
为了免去落人话柄,就让张虎和周实山带了份礼来姜家,就算有所交代了。
吴管家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恭恭敬敬地将三人迎了进去。
他们刚进前院,溶月远远地便瞧见她公婆和夫君已经等在前厅那里,见了她全都愣住,好似不认得她一样,反复上下打量了一番,又瞧见徐弘川没来,脸上难掩失望的神色。
溶月跟着陈氏往内院走去,姜元发和姜文诚则笑眯眯地把张虎和周实山迎入正厅招待。
陈氏眼红地打量着溶月一身华贵的装扮,她身上罩着石青色锦缎狐裘,里头是桃红色百蝶戏牡丹妆花缎大袖袄,下着湖绿色缠枝宝相花马面裙,一身袄裙领口、袖口和裙边都镶着一圈紫貂皮边,头上更是珠翠堆满,件件钗簪都镶着宝石,做工更是精致!
真是人要衣装,从前低眉顺眼的儿媳,如今尊贵又气派,活像个贵夫人!
陈氏脸上的笑是硬挤出来的,实际上快咬碎了一口牙,嫉妒得双眼发红,无法想象徐弘川府中是如何富贵泼天,瞧溶月头上戴的,身上穿的,都是她连见都没见过的好东西!
这小蹄子看来是得了宠了,那小畜生竟舍得给她穿这样名贵的衣裳!
陈氏领着溶月直接去了自己屋,待她脱下大氅、给自己行了礼后,又挤出个笑来,指着桌上堆着的四五个锦盒说道:“今日簪花宴,你两个舅父也来了,毕竟是姜家的大事。这是你两个舅父专门给你的,你在徐府当差,是姜家的功臣,姜家阖家老小都指望着你呢。”
溶月静静地听着婆母的话,轻轻瞥了一眼那几只锦盒,只是挺直了腰身却并未答话。
如今她站在陈氏面前,面对陈氏那张刻薄丑陋的脸庞,虽然心里头是说不出的憎恶,但却再无从前的忐忑和惧怕。
连她自己都讶异于这种变化,她从未想过有一天她能不卑不亢地平视她这位婆母,不必做小伏低、低眉顺眼!
陈氏见溶月一副云淡风轻的姿态,双眼沉着淡然,心里倒生出几分忐忑来。
果真是徐府待久了,还真是装得像个贵人!
陈氏尴尬地轻咳一声,扶着圈椅的扶手坐了下来,示意赵嬷嬷把锦盒打开,然后又接着说道:“这是两只福字纹金镯,一副如意云纹金项圈,还有两支石榴松鼠金步摇。哦对了,你两个舅父还拿了几匹缎子给你,我瞧着那花色好,便拿去做了几身衣裳。”
溶月只随意瞥了一眼那几件首饰,如今在徐府见多了名贵器物,那几件东西瞧着分量不少,做工却粗糙,连红杏头上戴的金钗都比那几个好看些。
她心中暗自冷笑,她这个婆母平日一毛不拔,她娘家兄弟送礼给她,想必是与徐弘川有关。
她平静地答道:“媳妇无功不受禄,不敢收两位舅父的礼。”
陈氏见她推脱,干笑两声:“你这孩子还客气什么,舅父给你的你就拿着,都是自家人。”
溶月腰杆挺得笔直,并没有收下的意思,也不搭话,明摆着态度冷淡,陈氏心里突然一沉,不悦地眯起三角眼。
几日不见,果然是仗了那小畜生的势,在她面前都敢拿乔了!
作者:
我们溶宝如今可是有靠山了吼吼~~~~~~~
背靠大树好乘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