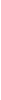可周佞不敢。
他知道关山月在疗伤,知道关山月一定会回来,知道关山月回来后想做什么,甚至于只要周佞想知道,就一定能事无巨细地知道关山月的一切。
可周佞不敢——他选择让关山月独自一个人疗伤。
然后自己为关山月扫清北城的一切障碍,等关山月回来开启她任何方式的计划,而每一个计划,周佞都打好了草稿,并为之做好了保障。
他守着这里,等关山月回来。
“可是我唯独没有想到,阿月。”周佞哑哑,“原来真的哪怕有那么一次我选择奋不顾身,都可以去救你。”
波涛汹涌的思绪一重又一重的席卷他、吞噬他。
原来那么多张被撕毁、过期的机票,哪怕有那么一次踏上飞机,周佞都能知道原来所有人都以为关山月过得很好的那五个岁月里——
关山月独自一人,困在绝望的野火上热燎,没有一缕柔风来吹去她的荒芜。
这场火中,烧没了关山月仅存的丁点善意,只余一片荒原。
那是关山月离开的这五年里,独自一人的野蛮生长。
“那份送到我桌面上的文件,有整整三十一页。”
不知过了多久,周佞终于再度开口,他颤着,仿佛最后一丝理智已经被击溃:
“三十一页,阿月,每一个字,都是对我的凌迟。”
关山月的唇被她死死咬得发白,几乎破皮。
五年前,关山月义无反顾般踏上的飞机似乎是盛大的出逃、她想逃离北城,想丢下所有的一切,是那个夏夜里最汹涌与震动的雨浪与默剧。
从小到大,关山月知道所谓亲情是假的、所谓父母对子女的爱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备选,从根就腐烂,亲情无法成为执着的纽带。
她见到的世界,从来都没有一点善意。
她不信爱,也不想侮辱爱这个字。
五年里有很多很多个深夜,关山月都曾经想过抛下一切——可是到最后那一步,关山月却还是退缩了。
算了吧。
她想。
没有人知道,最懦弱的那个,其实是关山月。
“那份文件上的每一个字都认识,可是合在一起,我根本就看不懂。”周佞几乎是气音,“我看不懂,我不懂,我不敢去想——”
“那么多个日夜里,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啊?”
周佞去加州,走过了关山月走过的每一遍路,他去了关山月租住的别墅,去了她念书的地方,也去了出事的邮轮,以及——
那份文件上描述的每一个地方。
最后,周佞近乎失神般在关山月曾经住过的别墅中,对着花园里那一大片已然枯萎的蔷薇,红了眼眶。
“阿月。”
周佞一寸寸松开自己的手,而后他抬起关山月的下巴,四目相对间,像在望一簇在凛冽中将折的春,颤颤着、就要折断:
“我来晚了,是不是?”
目光如汹涌着的黑色浪潮吞没着关山月,像是要将她沉入似梦的癫狂世界,紧紧缠上她的手脚,要沉入深海。
难以沾捉的情爱显形。
关山月动了嘴唇,可她到底是什么都没有说。
“在我回来之后,第一个见的人,并不是你。”周佞就这么看着她,颤声,“是薛幼菱。”
关山月瞳孔微缩。
薛幼菱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的消息,凌晨四点蹲在机场,将失魂落魄的周佞带走。
然后——
“她跟我说了一切。”周佞轻声。
她说了那天单独跟关山月聊天时,关山月透露的所有。
那么多字句被薛幼菱的哭腔死死塞进周佞本就混沌的脑海,到最后,周佞却只记得薛幼菱一句话:
“月月她说,你不可以爱她——会被毁了的。”
她说周佞,月月说不会爱人。
她说周佞——
你救救月月吧。
求你了。
所有亲近的人都看得出来,关山月几乎真的要溺死在那无边的苦海里了。
可是关山月那副淡漠无情的皮囊仿佛要将所有人都拒之门外,可那残缺的灵魂分明每一层都在叫嚣着——
来爱我呀。
为什么没人爱我。
为什么这个世界不能对我好一点。
为什么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对我好一点。
命运从一开始,就没有眷顾过她。
可她分明,什么都没有做过。
周佞强势出现,进驻关山月的人生,关山月窥见最初的灵光,她陷在了那年雪夜里周佞眼中闪烁的光——那是她最渴望的东西。
后来,她的理由让周佞觉得可笑后,却只剩一片悲鸣——
关山月只是觉得,他、连带着薛幼菱她们,都不应该被自己扯进那个地狱。
关山月只是觉得,既然神明从不爱她——
那仅仅不要爱她就好了。
是她作茧自缚。
关山月知道所有一切爱意,可就如同明婷那个诅咒一般:
“我对你最深的诅咒,是你明明眼睁睁看着有那么多人在爱你,可你永永远远都没办法弯下腰,去触碰、得到那万分之一的爱!”
“你活该永远孤寂。”
那就,不需要爱吧。
关山月如是想到。
周佞只觉那颗心被反复煎熬,痛得几乎感受不到四肢的存在,他只是那么看着关山月,是呢喃:
--
他知道关山月在疗伤,知道关山月一定会回来,知道关山月回来后想做什么,甚至于只要周佞想知道,就一定能事无巨细地知道关山月的一切。
可周佞不敢——他选择让关山月独自一个人疗伤。
然后自己为关山月扫清北城的一切障碍,等关山月回来开启她任何方式的计划,而每一个计划,周佞都打好了草稿,并为之做好了保障。
他守着这里,等关山月回来。
“可是我唯独没有想到,阿月。”周佞哑哑,“原来真的哪怕有那么一次我选择奋不顾身,都可以去救你。”
波涛汹涌的思绪一重又一重的席卷他、吞噬他。
原来那么多张被撕毁、过期的机票,哪怕有那么一次踏上飞机,周佞都能知道原来所有人都以为关山月过得很好的那五个岁月里——
关山月独自一人,困在绝望的野火上热燎,没有一缕柔风来吹去她的荒芜。
这场火中,烧没了关山月仅存的丁点善意,只余一片荒原。
那是关山月离开的这五年里,独自一人的野蛮生长。
“那份送到我桌面上的文件,有整整三十一页。”
不知过了多久,周佞终于再度开口,他颤着,仿佛最后一丝理智已经被击溃:
“三十一页,阿月,每一个字,都是对我的凌迟。”
关山月的唇被她死死咬得发白,几乎破皮。
五年前,关山月义无反顾般踏上的飞机似乎是盛大的出逃、她想逃离北城,想丢下所有的一切,是那个夏夜里最汹涌与震动的雨浪与默剧。
从小到大,关山月知道所谓亲情是假的、所谓父母对子女的爱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备选,从根就腐烂,亲情无法成为执着的纽带。
她见到的世界,从来都没有一点善意。
她不信爱,也不想侮辱爱这个字。
五年里有很多很多个深夜,关山月都曾经想过抛下一切——可是到最后那一步,关山月却还是退缩了。
算了吧。
她想。
没有人知道,最懦弱的那个,其实是关山月。
“那份文件上的每一个字都认识,可是合在一起,我根本就看不懂。”周佞几乎是气音,“我看不懂,我不懂,我不敢去想——”
“那么多个日夜里,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啊?”
周佞去加州,走过了关山月走过的每一遍路,他去了关山月租住的别墅,去了她念书的地方,也去了出事的邮轮,以及——
那份文件上描述的每一个地方。
最后,周佞近乎失神般在关山月曾经住过的别墅中,对着花园里那一大片已然枯萎的蔷薇,红了眼眶。
“阿月。”
周佞一寸寸松开自己的手,而后他抬起关山月的下巴,四目相对间,像在望一簇在凛冽中将折的春,颤颤着、就要折断:
“我来晚了,是不是?”
目光如汹涌着的黑色浪潮吞没着关山月,像是要将她沉入似梦的癫狂世界,紧紧缠上她的手脚,要沉入深海。
难以沾捉的情爱显形。
关山月动了嘴唇,可她到底是什么都没有说。
“在我回来之后,第一个见的人,并不是你。”周佞就这么看着她,颤声,“是薛幼菱。”
关山月瞳孔微缩。
薛幼菱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的消息,凌晨四点蹲在机场,将失魂落魄的周佞带走。
然后——
“她跟我说了一切。”周佞轻声。
她说了那天单独跟关山月聊天时,关山月透露的所有。
那么多字句被薛幼菱的哭腔死死塞进周佞本就混沌的脑海,到最后,周佞却只记得薛幼菱一句话:
“月月她说,你不可以爱她——会被毁了的。”
她说周佞,月月说不会爱人。
她说周佞——
你救救月月吧。
求你了。
所有亲近的人都看得出来,关山月几乎真的要溺死在那无边的苦海里了。
可是关山月那副淡漠无情的皮囊仿佛要将所有人都拒之门外,可那残缺的灵魂分明每一层都在叫嚣着——
来爱我呀。
为什么没人爱我。
为什么这个世界不能对我好一点。
为什么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对我好一点。
命运从一开始,就没有眷顾过她。
可她分明,什么都没有做过。
周佞强势出现,进驻关山月的人生,关山月窥见最初的灵光,她陷在了那年雪夜里周佞眼中闪烁的光——那是她最渴望的东西。
后来,她的理由让周佞觉得可笑后,却只剩一片悲鸣——
关山月只是觉得,他、连带着薛幼菱她们,都不应该被自己扯进那个地狱。
关山月只是觉得,既然神明从不爱她——
那仅仅不要爱她就好了。
是她作茧自缚。
关山月知道所有一切爱意,可就如同明婷那个诅咒一般:
“我对你最深的诅咒,是你明明眼睁睁看着有那么多人在爱你,可你永永远远都没办法弯下腰,去触碰、得到那万分之一的爱!”
“你活该永远孤寂。”
那就,不需要爱吧。
关山月如是想到。
周佞只觉那颗心被反复煎熬,痛得几乎感受不到四肢的存在,他只是那么看着关山月,是呢喃:
--